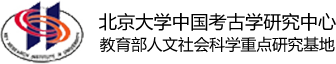优秀论文
返回冯峰:说“醴壶”
发布时间: 2018-02-10 来源:纸上考古
2002年,山东枣庄东江春秋墓地M2出土一对“邾君庆”壶,其铭文共16字:邾君庆作秦妊醴壶,其万年眉寿永宝用。器形、铭文相同的铜壶还有4件,系同一墓地盗掘出土[2]。6件“邾君庆”壶年代均为春秋早期,其自名“醴壶”,说明它们是用以盛醴的器具。 邾君庆壶及铭文 周代的“醴壶”,除了邾君庆壶外,尚有9件(组)。其基本信息见下表: 醴常被视为酒的一种,其酿造时间较短,浑浊而味甜。《说文解字·酉部》:“醴,酒一宿孰也。”《左传》哀公十一年孔颖达疏引郑玄曰:“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也。”《释名·释饮食》:“醴,体也,酿之一宿而成体,有酒味而已也。”它与一般的酒的差别,在于酿造方法上醴以“蘖”而酒以“曲”(《吕氏春秋·重己》高诱注:“醴者,以蘖与黍相体,不以曲也,浊而甜耳。”) 不过,在周代文献中,酒、醴常并称,区别明显: 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 (《诗经·行苇》)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 (《诗经·丰年》、《载芟》) 奠脯、醢、醴、酒。……执醴先,酒、脯、醢、俎从。 (《仪礼·士丧礼》) 两甒:醴、酒,酒在南。 (《仪礼·既夕礼》) 若不醴则醮用酒。……醴辞曰:“甘醴惟厚……”。醮辞曰:“旨酒既清……” (《仪礼·士冠礼》) 这说明在周人看来,醴并不属于酒,二者是并列关系。有学者认为:“先秦文献中,酒的名称很多,……其实就酿造方式来说,大别之,不外两类:其一,醴类;其一,酒类。”[13]其说可从。根据酿造所用谷物的不同,“醴”又有“稻醴”、“黍醴”和“梁醴”等几类(《礼记·内则》);作为周代主要饮品之一,它广泛应用于当时的礼仪活动[14]和日常饮食[15]中。据《仪礼》,“甒”是盛醴和酒的主要器具[16]。而文献记载周代盛酒多用壶,如《诗经·韩奕》“清酒百壶”,《仪礼·聘礼》“醙、黍、清皆两壶”。因此理论上讲,醴也可以壶盛之。上述10件(组)“醴壶”,就证明了周代铜壶可用来盛醴。 周代醴壶及其铭文 上左:仲多壶 上中:伯庶父壶 上右:郑楙叔宾父壶 中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曾伯陭壶 中中:杨姞壶(之一) 中右:蔡公子叔汤壶 下左:彭伯壶 下中:伯公父壶盖 下右:吕季姜壶(铭文摹本) << 左右滑动每张图片,可切换器物/铭文 >> 10件(组)“醴壶”,年代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有8件(组)可见壶身,1件只见壶盖(伯公父壶盖),1件器形不可见(吕季姜壶)。其共同特征是:一,均为圆壶(吕季姜壶未见器形,但据描述“器高一尺一寸,圜而有盖”,可知为圆壶);二,壶身可见者均为兽首半环形耳圆壶,细长颈,垂腹。在上述可见壶身的“醴壶”中,有6件(组)可根据纹饰风格分为三类: 甲类:伯庶父壶。腹部有络带纹,将壶身分为八部分;络带相交之处有方锥或三角锥形凸起。 乙类:邾君庆壶和曾伯陭壶。腹部饰两周宽波带纹,口沿下也有一周波带纹。 丙类:杨姞壶、蔡公子叔汤壶和彭伯壶。颈部以下饰瓦棱纹,有的间以窃曲纹、重环纹等其他纹饰。 三类纹饰风格的铜壶在周代兽首半环形耳壶中为常见之器。与甲类壶风格近似之器有周原庄白窖藏所出十三年壶[17]、董家窖藏所出仲南父壶[18]和强家M1出土之壶[19],均为西周中期后段(或稍晚)器,伯庶父壶也大致铸造于这个时期。与乙类壶纹饰接近之壶可举出周原庄白窖藏出土的三年壶[20]、齐家窖藏出土的几父壶[21]和师望壶[22]、番匊生壶[23]等器;这类壶时代一般为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个别区域(如齐地)可延续至春秋中晚期甚至战国(如洹子孟姜壶、陈喜壶)。与丙类壶风格相近者出土于黎城西关M8(楷侯宰壶)[24]、三门峡上村岭M2011[25]、新野小西关墓[26]和随州桃花坡M1[27]等墓,也见于新郑李家楼大墓[28]和中行遗址器物坑[29];此类壶主要见于两周之际或春秋早期,直到春秋中期晚段还有存在。 仲多壶和郑楙叔宾父壶纹饰风格较特殊,尚未见相近之器。 兽首半环形耳的青铜圆壶流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个别晚至春秋晚期以后)[30],有自名者已知约有34件(组)(附表一[31]),自名有“壶”、“宝壶”、“尊壶”、“宝尊壶”、“旅壶”、“醴壶”、“媵壶”、“壶”等,其中“醴壶”有8件,占近1/4;其他壶自名均不涉所盛物,不排除也是盛醴之壶。另一方面,上文已经指出,自名“醴壶”之铜壶均为圆壶,又包涵了周代兽首半环形耳圆壶的几种主要的类型;而周代铜壶的另一大类方壶,无论是兽首半环耳方壶还是贯耳方壶,均无自名“醴壶”者(参看附表二[32])。因此,周代兽首半环形耳的圆壶可能就是用以盛醴的“醴壶”。 作为周代重要饮品的“醴”,最早见载于西周中期金文[33]。如:穆公簋盖铭“(王)夕飨醴于大室”(《集成》4191),师遽方彝铭“王在周康寝飨醴”(《集成》9897),三年壶“王在郑,飨醴”(《集成》9726),长盉铭“穆王飨豊(醴)”(《集成》9455)。穆公簋盖和师遽方彝学者考证为穆王时器[34];长盉和三年壶则为共王以后器,而从前者铭文可知穆王时确有“飨醴”之活动。记载“醴”的传世文献也无有确证能早至西周中期以前者[35]。兽首半环耳圆壶开始出现于西周中期,当非偶然[36]。这类壶中年代较早的络带纹壶多为西周中期器,其中董家窖藏出土的仲南父壶[37]双耳兽首为“鹿首”[38](或以为赤麂之首[39]),保留了较早时期的风格[40],时代可能早于伯庶父“醴壶”,即便很难早到穆王时,也应前距不远,不排除以后发现更早之器。兽首半环形耳圆壶应是由西周早中期的细颈贯耳垂腹圆壶(如保侃母壶[41]、姪妊壶[42]、孟父壶[43]、仲姞壶[44]和张家坡M275所出壶[45]等)发展而来。孟父壶为络带纹壶,从纹饰风格看当是仲南父壶等的前身,其自名“鬱壶”(盛鬱鬯之壶),非盛醴之器;洛阳北窑出土康伯圆壶盖也自名“鬱壶”,说明了当时部分圆壶的功用。西周早期和中期前段,尊、卣是最重要的“酒器”,元氏西张出土的两件叔父卣自名“小鬱彝”(同出之尊铭残缺,文字相同),说明尊、卣很可能是盛“鬱”之器[46]。但西周中期后段,尊、卣突然减少并逐渐消失,部分盛“鬱”的贯耳圆壶也发展为盛“醴”的兽首半环耳圆壶;这是耐人寻味的具有时代性的变化,可能始于穆王晚期到共王时期。 仲南父壶(之一) 根津美术馆藏鸟纹方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兽首半环形耳方壶流行时段与圆壶基本吻合,其最早出现的时间也是西周中期,日本根津美术馆所藏的一对鸟纹方壶[47]、[48]和清宫旧藏的一对周壶[49]大概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者;半环耳上的兽首均为“鹿首”,颈部和圈足纹饰也近似仲南父壶,应为同一时期的器物[50]。春秋中晚期之际到晚期前段,兽首半环形耳方壶为长尾兽形耳方壶所取代[51]。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兽首半环耳方壶和圆壶并存的主要阶段,在部分高等级墓葬(如三门峡上村岭M2001[52]、M2011[53]、M2009[54])二者共出[55],一般各出2件;礼县大堡子山盗掘出土的铜壶中,既有秦公所作方壶(目前可知至少有3件),又有同铭之圆壶(目前可知有2件)图[56]。至春秋中期的新郑中行器物坑,方壶和圆壶仍同出,只是方壶2件,圆壶只有1件[57]。方壶和圆壶的同时使用,在《仪礼》中有记载[58]: 司宫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 (《燕礼》) 司宫尊于東楹之西,两方壶……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 (《大射》) 三门峡上村岭M2001出土圆壶和方壶 礼县大堡子山盗掘出土的秦公圆壶与方壶 (图片依次是曾见于佳士得行之秦公圆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秦公圆壶、J.J.Lally旧藏秦公方壶) <<左右滑动图片查看更多>> 新郑中行器物坑K2出土的方壶和圆壶 <<左右滑动图片查看更多>> 上文已经提到,从文献记载看,酒、醴是周代礼仪活动中的两种最重要的饮品;醴的重要地位的确定很可能不早于西周中期。从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盛放饮品最重要的两种铜器就是兽首半环形耳的方壶和圆壶,它们的流行时代基本相始终。圆壶多自名“醴壶”,而方壶非但无称“醴壶”者,还有的铭文表明其“用盛旨酉(酒)”[59]。据上引《仪礼·士冠礼》文,“旨酒”即酒,与“甘醴”(醴)并称。因此,推断周代的兽首半环形耳圆壶和方壶分别为“醴壶”和“酒壶”是合理的。青铜壶在周代青铜器群中的地位非常显著,与鼎、簋同为高等级墓葬中不可缺少的核心随葬品;这与酒、醴在周代礼仪中的重要作用是吻合的。 上海博物馆藏殳季良父壶盖及其铭文 在讨论结束前,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1.西周中期后段到春秋中期,还存在少量非兽首半环形耳的圆壶,如长清仙人台M6、随州何家台、周家岗墓出土圆壶[60] 和传世的伯鱼父壶[61];伯鱼父壶为贯耳壶,其余皆环形或半环形耳。它们均成对出现在墓葬中,仙人台M6的一对壶还与一对兽首半环形耳方壶共出,除去双耳,壶身特征与同时期的兽首半环形耳圆壶并无明显区别。因此,它们在性质上也当属于“醴壶”。还需要提到的是,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贯耳方壶数量明显多于贯耳圆壶,它们的器身风格与兽首半环形耳方壶也无二致。上文推断“醴壶”和“酒壶”分别是兽首半环形耳圆壶和方壶,其实际包涵似可扩大。 2.春秋中晚期之际后,兽首半环形耳的方壶和圆壶逐渐消失,长尾兽形耳的方壶(出现于春秋中晚期之际)和圆壶(出现于春秋晚期)[62]成为高等级铜壶的代表,继而又出现了铺首圆壶。这些方壶和圆壶在功用方面是否还有之前的差异,有待进一步探讨。 3.在铜壶自名中,有“醴壶”而无“酉(酒)壶”,这种对“醴”的强调说明“醴”的地位不如“酒”,二者在重要性上既并列又略有差别。实际上,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方壶的地位都要略高于圆壶。《仪礼》记载“方壶”使用级别高于“圜壶”,考古发现的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高等级墓葬中方壶的随葬比例要明显高于圆壶[63]。 4.同时随葬兽首半环形耳方壶和圆壶的墓葬数量很少,目前已知只有三门峡上村岭M2001(虢季墓)、M2009(虢仲墓)、M2011(虢太子墓),大概还可算上随葬环形耳圆壶的长清仙人台M6[64]。这些墓葬随葬的鼎、簋均在7鼎6簋之上[65],等级甚高,三门峡三座墓葬的墓主为虢公或虢太子[66]。其他随葬铜壶的墓葬,包括晋侯墓(如曲沃北赵M8、M64、M93)、芮公墓(韩城梁带M27),则只随葬一种壶,或方或圆。这可能与当时的葬制有关,只有地位高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享有此待遇[67];其他人则最多只能随葬一种壶,虽然随葬一种壶并不代表墓主生前只能使用一种壶。 附表一 周代有自名的兽首半环耳圆壶 附表二 周代有自名的兽首半环耳方壶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化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0卷,因微信格式所限有所删改,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注释: [1] 枣庄市政协台港澳侨民族宗教委员会、枣庄市博物馆:《小邾国遗珍》,第34—3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枣庄市东江周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2] 枣庄市政协台港澳侨民族宗教委员会、枣庄市博物馆:《小邾国遗珍》,第83—9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3] 该器全形拓见周亚《〈愙斋集古图〉笺注》,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 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据清光绪十一年自刻木本影印),收入《金文文献集成》第八册,线装书局,2005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 [6]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华书局,2012年。 [7]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年。 [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 [9] http://www.imamuseum.org/collections/artwork/wine-container-yi-earl-zeng-zengbo-yi-hu. [10]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西周(二)》,文物出版社,1997年。 [11] Jassica Rawson and Emma Bunker,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青铜聚英:中国古代与鄂尔多斯青铜器展览),1990年。 [12] 河南博物馆:《群雄逐鹿——两周中原列国文物瑰宝》,大象出版社,2003年。 [13]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第4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14] 《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聘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诗经》之《吉日》《行苇》《丰年》《载芟》,均记“醴”之使用。西周金文及《左传》等文献有关于“王飨醴”的记载。 [15] 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载陈辕颇出奔郑,在路上其族人辕咺向其进献稻醴,显然是供其个人饮用。 [16] 《士丧礼》:“东方之馔两瓦甒,其实醴、酒。” [17]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四卷,第686—702页,巴蜀书社,2005年。 [18]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三卷,第374—384页,巴蜀书社,2005年。 [19]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九卷,第1792—1804页,巴蜀书社,2005年。 [20]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四卷,第662—674页,巴蜀书社,2005年。 [21]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一卷,第84—96页,巴蜀书社,2005年。 [22] 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34页壶6,文物出版社,1999年。 [23] 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32页壶5,文物出版社,1999年。 [24] 国家文物局主编《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4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彩版三六:2、3,文物出版社,1999年。 [26]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2),图版拾陆:1,文物出版社,1978年。 [2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第242—245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8] 河南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第118、119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彩版二一、二三、二五,大象出版社,2006年。 [30] 目前所见较晚的兽首半环耳圆壶有新郑李家楼大墓和中行器物坑所出圆壶,滕州薛故城M2、M4所出壶,沂水刘家店子M1出土“公”壶等,年代在春秋中期晚段至中晚期之际。但在齐地,波带纹圆壶延续时间较长,晚的可至战国,如陈喜壶,比较特殊。 [31] “附表一”和“附表二”中器物以自名分类,同一自名内以铭文字数多少为序;方便起见,著录信息主要是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简称《铭图》)的编号。“附表一”中未列入伯克壶,该壶貌似圆壶,但《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认为“《博古图录》所摹图像失真”,疑其原为方壶。 [32] “附表二”只收录了有自名的兽首半环形耳方壶,可见其自名“壶”、“宝壶”、“尊壶”与多数兽首半环形耳圆壶之自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附表一”圆壶有5件自名“旅壶”(贯耳的伯鱼父圆壶和伯泺父壶盖、宬伯壶盖也自名“旅壶”,均为圆壶),方壶则无此自名,有待进一步讨论。贯耳方壶也是周代常见之方壶,有自名者亦有十余件(组),为便于对应“附表一”圆壶,未列入“附表二”。 [33] 有学者认为,天亡簋铭“王又大豊”之“豊”即“醴”,还有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即有“醴”字,均缺乏证据。 [34] 李学勤:《穆公簋盖在青铜器分期上的意义》,《文博》1984年第2期。 [35] 《尚书·说命》“若作酒、醴,尔唯曲、糵”,貌似时代较早,但该篇公认为《尚书》中的伪篇,不可以此为据将醴的出现推到商代。《礼记·明堂位》所谓“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也难以相信。 [36] 目前尚不能肯定商代和西周时期无“醴”(或与之性质相近之饮品),但“醴”作为与酒并称、具有重要地位的饮品,不早于西周中期。 [37]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三卷,第374页,巴蜀书社,2005年。 [38] 这类“鹿首”装饰始见于殷墟后期,西周早期也较为常见;中期以后就较少见了,除了仲南父壶和下文所说的根津所藏方壶外,还有二十七年卫簋和辅师反簋等。 [39] [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第28—2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40] 此类兽首半环形耳的圆壶还有传山西吉县、洪洞一带出土的汤伯壶(《铭图》12172)。 [41]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器138,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42] 《铭图》12149。 [43] 罗振玉:《贞松堂吉金图》,第93—94页,台联国风出版社,1978年。 [44] 《铭图》12257。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彩版4: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6] 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47] 根津美術館《館藏殷周の青銅器》,器22、23,2009年。22器盖、器各有一字铭文,当系伪铭;23器即眉□壶。 [48]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西周(二)》,图版一三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即上注中的器22。 [49] 一件失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参看“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西周金文录》,第122—123页,“国立故宫博物院”,2012年(初版三刷)。另一件完整,即《铭图》12393,据称“现藏上海诚源文化艺术公司”。 [50] 此类兽首之方壶还有陕西延长出土的苏壶(《铭图》12343)。 [51] 较晚之兽首半环耳方壶出土于辉县琉璃阁甲、乙墓,洛阳体育场路西M8832、M8821,洛阳613研究所C1M6112,长治分水岭M269、M270,海阳嘴子前M4等墓葬,时代为春秋中晚期之际到春秋晚期前段。春秋中晚期之际和晚期前段开始出现的新风格的长尾兽形耳方壶,有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两种方壶、上马M13所出方壶等。关中秦墓出土“明器”方壶则延续时间要更晚一些。 [5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5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54] 上村岭M2009虢仲墓材料未正式发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考古河南》(大象出版社,2012年)发表了该墓所出的部分器物的图片,虽不包括铜壶,但文字中指出该墓出有“方壶、圆壶”(第17页)。 [5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彩版六:3、4文物出版社,1999年。 [56] 图八:1、3分别采自李朝远《青铜器学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图一”、第98页“图七”。图八:2采自吕章申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萃》,第143页图,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年。 [5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彩版二〇、二一,大象出版社,2006年。 [58] 有学者认为,《仪礼》中的“方壶”和“圜壶”为“瓦器”,即陶器,不确。首先,《仪礼》中的器具,若为“瓦器”,一般会注明,如《燕礼》《聘礼》有“瓦大”,《士丧礼》有“瓦甒”、“瓦敦”,《少牢馈食礼》有“瓦豆”;其次,《燕礼》《大射》均为周代国君主导的高等级礼仪,使用青铜器乃当然之事;第三,考古发现中只有青铜器既有方壶也有圆壶,陶器则多见圆壶而基本不见方壶。 [59]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西周篇(下)》,器三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60]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大学博物馆:《山东大学文物精品选》,器56,齐鲁书社,200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第222—225、284—28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6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704、A705,科学出版社,1962年。 [62] 如传汲县出土的赵孟疥壶和太原金胜村墓地出土之壶。 [63] 这些高等级墓葬随葬铜壶以方壶为主,如三门峡上村岭虢墓,随葬铜壶的完整墓葬不少于10座,其中M2001、M2011、M2009同时随葬方壶和圆壶,其余墓葬除M2006随葬圆壶外,均只随葬方壶。 [64]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65] 上村岭M2001随葬7鼎6簋,M2011随葬7鼎8簋,M2009“铜鼎有30件、铜簋有27件之多”;长清仙人台M6随葬15鼎8簋。 [66] 上村岭 M2009墓主虢仲为一代虢公当无问题;M2001墓主许多学者认为也是一代虢公,即便不是,也是地位接近虢公的高等级人物;虢太子地位近于君,有的太子甚至死后被追封君,如秦静公。 [67] 虢公高于等一般诸侯,虢太子级别有不会太低。《左传》庄公十八年:“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可知虢公地位高于晋侯。
-

-

-

-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邮编:100871
邮箱:webmaster@pku.edu.cn
-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
京ICP备05065075号-1
京公网安备 110402430047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