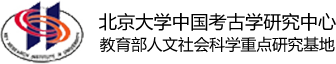中心活动
返回做时代最好的学术,走进学科史 ——建设“北大中国考古学书系”
发布时间:2020年6月9日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微信公众号
沈睿文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一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我以为:
首先,要让后学者感受到学术研究之美,让后学者从各位老师的撰述中,能感受到你们的“大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照,乃至对人类命运的关照和悲悯之心。这就是考古学研究的壮阔和美丽。只有让后学者从中感受到考古学的“大美”和学术尊严,感受到你们笔触背后的“温暖”和“大爱”,考古学才有可能也成为他们一生的追求和事业。考古学也才能由此实现它教书育人的使命。
其次,在学术和研究方法上开一代新风。考古学是一门“日日新”的学问,既要从新资料来探讨新问题,也要从旧资料中发现新课题。我们的学术、我们的教材不仅要拥有创造性的见解、具有学术预见性,而且要有学科新领域的开拓,更要有方法、理论的创新。这一点,宿白先生的佛教石窟寺考古研究、藏传佛教寺院研究就是典型的范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有足够的学术自信和学术定力。我们需要在学科研究领域、学科方法和理论方面都有所开拓,而不只是一味地跟着他人、跟着外国学者走。人家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人家测什么数据、我们就跟着测什么数据。我们更需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弄清楚现阶段我们自己的、对考古学科有深远影响的、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考古学者要有自己的考古学重大问题,能产生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与技术、方法。在解决中国考古学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在学科方法和学理方面也有所突破、有所推进。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从自身内部迸发出来的学术创造。这一点,我对我们的老师充满信心。
第三点,具体如何来写?在中华书局1982年新版的两卷本《隋唐史》中,岑仲勉自己说这套讲义的“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庶学生将来出而执教,不至面对难题,即从事研究,亦能略有基础”。我想,岑仲勉的这个主张同样可以作为我们写作“北大中国考古学”书系的具体指导意见。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我们对同行学术研究的尊重和学术道德的恪守。
“北大中国考古学”书系要成为后学者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和指引,其中所表达的必须是正确的学术理念,绝不做出任何不切实际的结论。要反复锤炼,不断萃取。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论断——如同先生们的教材和著作一样。
尊师重教,是我们学院的优良传统,需要代代传承下去。先生们给我们缔造的优秀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传统,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发扬光大,更要再塑造,继续在学术和研究方法上独领风骚。
配合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进一步系统完善中国考古学书系。“北大中国考古学书系”的建设便是我们教学、传承,研究、创新的过程。在该书系中体现我们北大考古学者对考古学科的新思考和新理念。教学相长,充分体现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这要求各位老师全身心地投入到备课和讲授中去。这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新见解,得出新结论,重新写作的过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实践、理论学习和科研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相互提高,成就经典。
我们学院的老师们个个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每位都是一座知识的宝藏,令人高山仰止。但我以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天职就是创造新知、创造新见,而不只是口若悬河、只是站在边上指点“江山”,自己读书、自己明白而已。国家、人民用血汗供养我们,我们要懂得回馈他们。否则,便就真地成为彻头彻尾的“自私分子”了。
年富力强、思维强健,正是系统表达自己学术之时。从目前学院教员的年龄结构来看,特别是40-60岁之间的老师要勇于担当教材书系的写作。团队写作、个人独立承担的方式都可以。通过教材写作,也是学院教学、科研团队以及优良传统传、帮、带的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院也要充分发挥老教师的指导作用。“全民皆兵,同仇敌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1954年5月,宿白先生(1922-2018)完成《白沙宋墓》的编写,时年32岁。1957年9月初版,时年35岁。这是宿先生的名山之作,由此奠定了宿先生一生的基业。1951年,宿先生发表了《中国石窟寺研究》系列研究中的第1篇,时年29岁;1996年,他完成23篇的结集出版,时年74岁;
1955年,田余庆先生(1924-2014)写《中国古代史纲要》“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也就32岁。1979年,田先生发表了《释“王与马共天下”》(《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时年55岁。1989年,他完成《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版,时年65岁。从《东晋门阀政治》的写作里面,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田先生对东晋社会的悲悯之心;
1939年,钱钟书(1910-1998)开始《谈艺录》的写作,时年28岁。此时他差不多已确立了一生的学术风格(余英时语);
巴金(1904-2005)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曹禺(1910-1996)“生命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大都完成于30岁左右。
说句开玩笑的话,等我们都上了岁数,便多半写不动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剩下的只能是编著、编书了,再不是著书立说了。
我们都是在先生们的福荫和庇护下才得以成长的。那么,同样地,我们应该给后来者留下什么?我认为,“北大中国考古学书系”,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应该留给学院的资产,而且责无旁贷。为此,学院党政班子也多次开会,反复讨论,下大决心制定措施给予助力。
我们的先生们已经永远长存于学科史中,只有我们跟随先生们的足迹——从学术史走进学科史,北大考古学才能继续它的辉煌,继续保持它的学术尊严和荣光。也惟有如此,北大考古才有可能继续引领中国考古学。
在此,我再次代表学院行政班子向参与、和即将参与到“北大中国考古学书系”建设中的老师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请允许我代表以后即将在你们福荫和庇护下的北大考古师生们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谢谢你们,北大考古未来的先生们!
2020年6月9日
-

-

-

-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邮编:100871
邮箱:webmaster@pku.edu.cn
-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
京ICP备05065075号-1
京公网安备 110402430047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