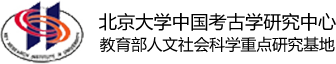成果展示
返回倪润安:北源与南源——后蜀墓葬形制演变过程研究
发布时间:2021年4月20日 信息来源:纸上考古
倪润安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摘要:后蜀墓葬形制别有特色,汇聚了南、北两源的文化因素。南源是中晚唐经前蜀以来的蜀地自有墓葬文化,北源则与建国者孟知祥所率北来集团的后唐文化因素有关。孟知祥将后唐中原地区的单主室圆形墓引入蜀地,建造了和陵。能够反映后蜀墓葬深刻变化的是Ca型与A型墓葬之间的替变。Ca型墓葬是大型长方形单主室墓,并在两侧壁和后壁各开有一个龛室。此型墓葬的存在,表明后主执政前期北源因素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A型墓葬是前、中、后三室墓,源自前蜀,属于南源因素,在后主执政后期成为墓葬主流。
关键词:后蜀墓葬形制 北源 南源 后唐 前蜀
* 原文刊载于《考古》2021年第1期,作者授权“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刊发,如需引用请据纸版原文。
后蜀(公元934~965年)立国30余年,历二主而亡,国祚并不太长,然墓葬文化别有特色,汇聚了南、北两源的文化因素。南源是中晚唐经前蜀以来的蜀地自有墓葬文化,北源则与建国者孟知祥所率北来集团的后唐文化因素有关。南、北二源在后蜀墓葬中此消彼长,相互作用,映射着政治、文化的起伏转折。本文未遑及全面讨论后蜀墓葬文化,仅对其中形制演变过程略做探讨。
- 一、北源因素与后唐圆形墓在蜀地的出现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闰正月,孟知祥称帝于蜀,七月病故,陵曰和陵[1]。其妻福庆长公主是晋王李克用的长女、后唐庄宗之姊,死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2]。长兴四年(公元933年),明宗遣使追封她为晋国雍顺长公主[3]。
和陵为孟知祥夫妇合葬墓,位于成都市北郊磨盘山南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全为青石砌筑。墓道为阶梯式,共22级阶梯。墓门为仿木结构建筑,彩枋四柱,中间两柱上分别刻有青龙、白虎。门前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守门卫士圆雕石像。甬道为券顶,设有石闸门、双扇石门及覆马槽式排水沟各一道,墓门内侧至石门前的两侧壁上彩绘男、女侍者。墓室为一主室,两侧各有一耳室,平面皆呈圆形,主室直径6.7、高8.16米,二耳室均直径3.4、高6米,主室正中横陈须弥座石棺床(图一)[4]。

图一 孟知祥夫妇和陵平面图
该墓因福庆长公主去世而营建。福庆长公主墓志准确记载了她的亡故和下葬时间。墓志曰:“长兴三年正月十三日长公主享年六十,薨于正寝”,“长兴三年十一月廿四日葬于成都县会仙乡”。可知此墓修建于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从计划到完成约有10个月时间。这一过程应是在孟知祥决策之下进行,已经考虑到了合葬的需求。关于和陵形制的来源,有研究者指出其与北方地区隋唐五代圆形墓大同小异,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5]。这一观点敏锐指出了该墓的北方文化来源。在此,我们将进一步着重分析五代时期圆形墓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和陵产生影响的过程。
洛阳在五代前两个王朝后梁、后唐时期都曾是都城所在。这里的墓葬文化代表着国家的主流意识。而洛阳地区与圆形墓葬发生关系并不是从五代之初就有的。隋唐时期,圆形墓的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推进的态势。今辽宁朝阳地区,圆形墓在唐初开始出现,流行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安史之乱以后基本消失[6]。今河北北部地区(含京津地区)开始出现圆形墓是在唐高宗时期,中晚唐时期圆形墓大量出现,成为主流墓葬形制,内壁上有的绘有壁画,有的装饰砖砌仿木结构或砖雕家具[7]。唐代圆形墓在河北南部出现的很少[8]。离河北南部较近的洛阳地区在隋唐时期一直缺乏圆形墓。
以洛阳为中心的今河南地区,晚唐墓葬的形制结构既延续了中唐时期的风格,又出现了新的现象。继承中唐时期而来的特征,诸如墓道、甬道衔接在墓室南壁偏东处,平面作直背刀形;墓室形制多为竖长方形,四壁掏挖十二壁龛的习俗仍在延用等。新出现的墓形是梯形墓和双梯形墓,在晚唐墓中最具代表性[9]。晚唐墓葬的墓道除了斜坡式,更多的是竖井式。竖井墓道的底部常见斜坡,也有阶梯状。例如伊川鸦岭乡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齐国太夫人吴氏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带三个过洞、三个天井,墓室平面近竖长方形(图二,1)[10]。又如偃师杏园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密州莒县主簿韦友直墓,是刀形墓,竖井阶梯状墓道,墓室平面呈竖长方形(图二,2)[11]。又如偃师杏园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夏州馆驿巡官李端友墓,竖井斜坡式墓道,墓道与墓室均为北宽南窄的梯形,属于双梯形墓(图二,3)[12]。再如偃师杏园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怀州录事参军事李杼墓,竖井斜坡式墓道,墓道平面呈北宽南窄的梯形,墓室平面呈竖长方形(图二,4)[13]。

图二 洛阳地区晚唐墓葬
1. 伊川鸦岭乡齐国太夫人墓 2. 偃师杏园韦友直墓 3. 偃师杏园李端友墓 4. 偃师杏园李杼墓
后梁灭唐后,洛阳为其都城之一,而河北北部处于敌对者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控制下。圆形墓在后梁时期进入洛阳地区的可能性不大。洛阳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高继蟾墓[14],是竖井墓道单室土洞墓,墓道平面呈北宽南窄的梯形,墓室平面呈竖长方形(图三,1)。这近似于晚唐李杼墓的形制。高继蟾是梁教坊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地位较高。在洛阳龙盛小区还出土两座后梁时期的小型墓葬。M4531为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室平面呈梯形,北宽南窄(图三,2);M4539为刀形土洞墓,墓道完整形制不详,底部为阶梯状,墓室平面呈竖长方形(图三,3)[15]。这两座墓也都继承了晚唐墓葬的特点。可见洛阳后梁墓葬基本上延袭着晚唐轨迹,没有引入圆形墓。

图三 洛阳地区后梁墓
1. 高继蟾墓 2. 洛阳龙盛小区M4531 3. 洛阳龙盛小区M4539
晋王李克用建极陵建于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位于山西代县七里铺村。该墓为单室石室墓,坐北朝南,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墓道未全部发掘,墓门位于甬道入口,以三块巨石板封门,外侧东、西两壁各有一座砖雕歇山顶建筑。甬道为石构,券顶,两侧壁上部各浮雕一组骑兵仪仗图,下部各浮雕一位头戴幞头、形体高大的男侍者,其身后为步兵仪仗图。墓室也为石构,平面呈圆角方形(图四),穹隆顶已毁,南北长9.45、东西宽9.65、残高5. 56米。墓室四壁砌筑十根上托仿木结构斗拱的立柱,立柱将东、西、北三壁各区隔为三个开间,均在正中开间雕刻饰有泡钉的大门。北壁正中开间的大门两侧各浮雕一位女侍者,两侧开间浮雕破子棂窗。东壁正中开间的大门北侧浮雕一位女侍者、南侧浮雕一位男侍者,北侧开间为浮雕方格窗,南侧开间无浮雕。西壁正中开间的大门北侧浮雕一位男侍者、南侧浮雕一位女侍者,北侧开间为浮雕方格窗,南侧开间无浮雕。墓室中央置有一座长方形石棺床,须弥座式,正面为束腰,雕有9个壸门,壸门内雕刻身披飘带的童子,余三面为垂直立面[16]。李克用墓室平面仍以方形为主体,但四壁弧起、四角圆弧,已呈现出向圆形墓转化的趋势。这应是受到了河北北部圆形墓的影响。

图四 晋王李克用建极陵墓室
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李存勖建立后唐,灭后梁,定都洛阳。这为河北圆形墓进入洛阳创造了条件。同光四年(公元926年)李存勖死于兵变,享国较短。后唐文化的发展主要是在继任的明宗时期进行。明宗在位的8年,史称“小康”,文化事业取得较大的成就[17]。后唐政权所倚仗的治国人才,一部分是晋王时代的旧部宿臣,另一部分主要是从河北北部的幽州流入的文士。幽州入后唐的文士,有赵凤、冯道、吕琦、刘去非等,对于后唐大事参谋较多,对其文化发展功莫大焉[18]。明宗即位之初,就重用来自幽州的文士。其中名声最大的是冯道,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即拜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19],成为宰相。圆形墓葬进入洛阳,并形成一定制度,最可能是在明宗时期。
目前还没有发现后唐时期的圆形纪年墓,但公元936年后唐亡后不久,洛阳后晋墓葬中就见到了圆形纪年墓,如伊川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乐安郡公孙璠墓[20]。孙璠墓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5.02~5.08米(图五,1);墓室壁面对称分布八根上托仿木结构斗拱的立柱,立柱之间的壁面有砖砌的灯擎、桌凳、柜、门扇、直棂窗等,墓顶绘日、月、星象图;墓室中央为双层的长方形砖棺床。此墓的壁面砖雕、棺床设置与建极陵相比,呈现出文化的延续性。在太原地区,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王氏小娘子墓[21]平面已近似椭圆形(图五,2),但可以看出有些壁面不够圆滑,呈现出明显的转角,实际上是一个将方向做了偏转的圆角方形墓,与建极陵一脉相承。墓室内有仿木结构砖雕彩绘,周壁砌六根上托仿木结构斗拱的红色立柱,将墓壁分隔为六部分,除南壁墓门两侧外,其余五壁间都有砖砌门窗;东、北、西三个较大的壁面设置仿木格子门,西北、东北二个较小的壁面设置仿木破子棂窗。这些壁面砖雕也与建极陵颇相似。上述两个墓例表明在后晋建立后不久洛阳地区就出现了成熟的圆形墓,太原地区也在向圆形墓转化。因此,洛阳地区圆形墓不会迟滞到后晋才出现,而应是出现在后唐,其特征当在建极陵与孙璠墓之间演变。

图五 后晋墓葬
1. 洛阳孙璠墓 2. 太原王氏小娘子墓
洛阳五代墓葬中也确实发现了这方面的线索,如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22]。此墓为阶梯墓道单室砖墓,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4.34~4.7米(图六,1)。墓室壁面砖雕有六根上托仿木结构斗拱的立柱,斗拱之间的壁面有砖砌的门、直棂窗、桌、椅、灯擎、柜、衣架。甬道东、西壁以及墓室在墓门两侧的壁面上均绘有壁画。甬道东、西壁各绘一名头戴翘角幞头、执棒的男性人物,代表仪仗出行,墓室在墓门两侧的壁面上各绘两个女侍。墓墓葬形制与后晋孙璠墓基本一致,出土的鎏金铜泡钉与后梁高继蟾墓铜泡钉形制相同,而浮雕与壁画的发展特点介乎于建极陵与孙璠墓之间。建极陵、龙盛小学壁画墓与孙璠墓之间,在仿木结构及附属设施上,龙盛小学壁画墓与孙璠墓接近,都有建极陵所没有的灯擎、桌、柜等;在人物图像上,建极陵和龙盛小学壁画墓都有仪仗出行图、侍从,前者为石雕,后者为壁画,后者的仪仗出行图简化很多,而孙璠墓已经没有人物图像。龙盛小学壁画墓的这些特点表明其年代应是在后唐时期。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图六,2)[23]、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24]、洛阳苗北村壁画墓[25]的形制、砖雕、壁画特征也与龙盛小学壁画墓相近,属于后唐的可能性大。

图六 洛阳地区后唐墓葬
1. 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 2. 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
和陵的建造,正值后唐明宗时期。此时孟知祥虽已存独立之心,但尚未与后唐决裂。因此,福庆长公主作为后唐宗室的重要成员,理应按照洛阳新形成的墓葬礼制进行安葬。从和陵的建成情况看,既与已知的洛阳圆形墓关系密切,又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圆形的墓葬形制,以及甬道两侧壁的男、女侍者壁画,都与洛阳地区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和陵墓室壁面为素面,没有雕刻上托仿木结构斗拱的立柱、门窗、桌椅、灯、柜等。还有一些特征显示出和陵比洛阳已知圆形墓的等级要高得多,主要有三点:一是主室直径6.7米,接近7米,而郡公级别的孙璠墓直径约5米,显然前者比后者的等级要高得多;二是墓葬为石构,主室内横陈的须弥座棺台也是石质,具有建极陵的传统。这大概是最高等级的墓葬才能使用的;三是在圆形的单墓室两侧各设一圆形耳室,而洛阳地区已知圆形墓只有单室,并无耳室,设耳室或许是更高等级的一种做法。这三点表明和陵的规格很高,或采用的是后唐皇室墓葬的形制。无独有偶,后唐德妃伊氏的墓葬可资佐证。伊氏被辽太宗耶律德光掠往契丹,辽会同五年即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去世,会同六年(公元943年)下葬。其墓室结构为一主室,左右各有一耳室,主室平面呈圆形,两耳室平面略呈梯形(图七)[26]。其墓葬形制是同时代与孟知祥夫妇和陵最为相似的。墓志记载德妃到辽国后,获得优待,“特令充赡给,降鸿私而迥异,方故国以无殊”,“藏事依中朝之轨式,表上国之哀荣”[27]。“藏事依中朝之轨式”,就是按当时中原的等级制度给下葬,所对应的就是后唐、后晋时期帝后等级的陵墓。

图七 后唐德妃伊氏墓平面图
- 二、后蜀南源因素的兴盛及其对北源因素的改塑
目前辨识的后蜀墓葬,全为砖室墓[28]。按墓室数量多少,其形制可分为三型。
A型:前、中、后三室墓。两侧壁开有耳室或小龛,有的还设有肋柱。根据尺寸大小,可分为两亚型。
Aa型:大型,墓室总长度在18米以上。例如广政十一年(公元948年)赠太子太师张虔钊墓,坐北朝南,阶梯墓道,全长约27米。前室长5.2、宽3.9米,两侧壁各有一耳室;中室长约10.6、宽5米,两侧壁各有三个耳室;后室长2.9、宽2.8米,两侧壁各有一进深很浅的拱形小龛。墓室两侧壁各有七根肋柱,中室内设有须弥座式石棺床(图八,1)[29]。又如广政十八年(公元955年)太傅、乐安王孙汉韶墓,坐东朝西,无墓道,前室前部被破坏,残长18.8米。前室残长5.1、宽3.65米,两侧壁微外侈,各有一长方形小龛;中室长约10、宽3.8~4.3米,两侧壁各有两个对称的方形耳室;后室长3.7、宽3米,两侧壁后部略向外敞,后壁向内凹成弧形。中室中部设有须弥座式石棺床 [30]。
Ab型:中型,墓室总长度在7~12米之间。例如广政十五年(公元952年)彭州刺史徐铎墓,南北向,无墓道,全长10.8米。前室长2.25[31]、宽2.2~2.4米,两侧壁微外侈;中室长约6、宽3.48米,两侧壁各有两个小龛;后室长2.5、宽2.1米;墓室两侧壁各有五根肋柱。中室设置有须弥座砖棺床(图八,2)[32]。徐铎妻张氏墓,南北向,无墓道,全长11.28米。前室残长约2、宽2.22~2.4米,两侧壁前段外侈;中室长约6.29、宽2.69米;后室长约2.15、宽2.1米;中室顶部彩绘壁画,中部设置有砖棺床 [33]。广政十八年(公元955年)宋琳墓全长7.64米[34],广政二十一年(公元958年)光禄大夫李韡墓全长约9米[35],也都是此型墓。

图八 A型后蜀墓葬
1. 张虔钊墓(Aa型) 2. 徐铎墓(Ab型)
B型:前、后双室墓。例如成都永陵公园M12,由东、西并列的两个墓室组成。东墓室为前、后双室墓,坐北朝南,前室平面呈长方形,长1. 51、宽0. 9米;后室平面呈梯形,长1. 56、宽0. 72~0. 82米。两侧壁无龛、无肋柱(图九)。东墓室出有一块买地券,记载墓主人为雷氏,年代为“广(政)二十六年癸亥” [36]。

图九 B型后蜀墓葬(永陵公园M12东墓室雷氏墓)
C型:长方形单室墓。根据尺寸大小,可分为两亚型。
Ca型:大型。两侧壁和后壁开有龛室,没有肋柱。例如广政十三年(公元950年)宋王赵廷隐墓,坐西向东,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及南、西、北三个龛室组成(图一〇,1)。墓道平面呈东宽西窄的梯形,东侧为斜坡状,底部近封门处呈阶梯状。甬道为券顶,平面呈长方形,墓室平面呈横长方形,顶部已垮塌,中部横置须弥座棺床。三个龛室结构基本一致,为券顶,平面呈长方形,且底部都高于前室约0.5米。墓门、墓壁及墓顶绘有壁画[37]。
Cb型:小型。墓室总长度一般在6米以内。墓室前端地面低于中、后部,两侧壁或后壁开有小龛或耳室,两侧壁还设有肋柱。例如成都西窑村M21,坐西朝东,全长3.26米,墓室前端地面比中、后部低0.22米,两侧壁靠前端各开有一小龛,相互对称,两侧壁还各砌筑有四根肋柱(图一〇,2)[38]。该墓出土一方石质买地券,铭文可辨“广政……丁巳四月……”字样,对应广政二十年(公元957年)[39]。成都近郊广政十四年(公元951年)墓,坐北朝南,全长约6米,两侧壁后端及后壁各开有一耳室,两侧壁还各砌筑有五根肋柱[40]。成都清江路2000CHQM2、2000CHQM4[41]也属此型。

图一〇 C型后蜀墓葬
1. 赵廷隐墓(Ca型) 2. 成都西窑村M21(Cb型)
以上墓葬形制中,B型、Cb型与中晚唐以来本地墓葬之间,A型与前蜀墓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南源文化渊源。
后蜀B型墓葬平面呈前、后双室结构,前室为长方形,后室为梯形。这种形制在成都地区当地可追溯到中唐时期,经晚唐延续到五代。中晚唐时期的墓葬形制通常前、后室平面都呈梯形。如中唐或略晚的青白江区武海·中华名城M1(图一一,1)[42]、中晚唐之际的高新区紫荆路M1(图一一,2)[43]、中晚唐时期的成都清江路2000CHQM3[44]、唐末至五代的高新区紫荆路M2(图一一,3)[45]。前两座墓例设有可与前室相区分的甬道,甬道底部会比墓室底部低一些。后两座墓例没有设置甬道,而让前室前端的底部比墓室其他部分的底部低一些。设甬道的做法较早,晚唐以后基本消失。也有些墓例是墓室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如中唐或略晚的青白江区武海·中华名城M2(图一一,4)[46]、晚唐至五代青白江区和平村M13[47]。这两例与后蜀B型墓葬形制已几乎相同了。

图一一 成都地区唐至五代墓葬(一)
1. 青白江区武海·中华名城M1 2. 高新区紫荆路M1 3. 高新区紫荆路M2 4. 青白江区武海·中华名城M2
后蜀Cb型墓葬的特征也可追溯到成都地区的中唐墓葬,并延续到后蜀建立前夕。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爨公墓,全长6.82米,主室平面呈长方形,两侧壁中部各开一耳室,主室和两耳室的后壁各开一龛,主室前端的地面低于中、后部。特征与后蜀Cb型墓葬基本一致。略有不同之处在于耳室后壁又设龛,显得较为复杂,同时侧壁上砌筑肋柱的情况并不普遍,仅在主室与耳室结合部的转角两侧设置(图一二,1)[48]。到晚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王怀珍墓,无墓道,全长4.96米,两侧耳室后壁不再设龛,仅主室后壁设一龛,且主室两侧壁普遍设置肋柱(图一二,4)[49]。这已与后蜀Cb型墓葬特征基本一致了。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鲜腾墓,无墓道,全长4.36米,主室后壁无龛,侧壁也没有肋柱,其他特征与后蜀Cb型墓葬相同(图一二,5)[50]。晚唐时期,还出现了并穴双室墓,各室特征与后蜀Cb型墓葬相似。如成都龙泉驿区洪河大道南延线M12,并列的双室特征完全相同,两侧壁前端和后壁各设一龛,两侧壁各设置四道肋柱,墓底前后部在同一平面上。东室遭到破坏,西室全长2.98米(图一二,6)[51]。前蜀时期的并穴双室墓,有乾德五年(公元923年)魏王王宗侃夫妇墓,两室特征相同,均呈竖长方形,长10.38米,墓底前后部在同一平面上,墓室中部均设有一座竖长方形砖棺床。两室的后壁不设耳室或龛,两侧壁本各设一个耳室,但因两室互通,相通侧壁的两个耳室合二为一,但又在中间设一道分隔墙,保留了这个共同耳室原本形态的痕迹;墓室两侧壁各有四道肋柱,耳室两侧壁各有三道肋柱(图一二,2)[52]。广汉烟堆子M3也是并穴双室墓,坐北朝南,东、西并列两墓室,每室南侧均有对应的阶梯式墓道,全长9. 15米,墓室长4. 65米。两墓室平面均呈竖长方形,前端地面低于中、后部,东墓室东侧壁尚可见五道肋柱,东墓室东侧壁、西墓室西侧壁各开一耳室。两墓室北端设有龛,均为仿木结构(图一二,3)[53]。该墓设置仿木结构的龛,可能与“河北因素”的影响有关[54]。而且该墓的阶梯式墓道在蜀地也显得十分独特,倒是在洛阳地区后唐墓葬中常见(见图六,1、2)。这座墓的形制是北方因素与当地因素结合的产物。由此,我们推断其年代很可能是在后唐占领蜀地时期。

图一二 成都地区唐至五代墓葬(二)
1. 成都桐梓林村唐代爨公墓 2. 成都龙泉驿区前蜀王宗侃夫妇墓 3. 广汉烟堆子M3 4. 成都红色村唐代王怀珍墓 5. 成都金沙村唐代鲜腾墓 6. 成都龙泉驿区洪河大道南延线唐墓M12
前、中、后三室的后蜀A型墓与前蜀墓葬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然而前蜀墓葬中出现三室墓,并非凭空而造,仍是承袭了蜀地中晚唐墓葬的基本结构。晚唐王怀珍墓的墓室结构总体是单室墓,但墓室前端设计成低凹部分,放置有石墓志、瓷器等。墓室的中后部较高,前端断面设计有上、下两层壸门,表明这一部分是棺床空间。墓室的后壁辟有一个龛室,底部高于墓室的底部,发现一件陶提梁壶,表明龛室里可能也是放置随葬品的(见图一二,4)[55]。由于王怀珍墓全长只有4.96米,墓室内虽可划分为三部分,但尚不足以独自成室。前蜀三室墓则是将这三部分的区划加以强化和扩展,随着墓葬总长大大增加,各部分得以分别成室。同时,晚唐墓葬两侧壁设置耳室或龛、肋柱的特征,也被前蜀三室墓所继承。前蜀三室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前蜀建国、墓葬等级需要提高的礼制问题。代表性墓葬有光天元年(公元918年)皇帝王建永陵[56]、乾德五年(公元923年)弘农王晋晖墓[57]等。永陵墓室全长30.8米,室内长23.4米,两侧壁各设有十四道肋柱(图一三)。晋晖墓中室后部和后室长度不详,墓葬总长应在12米以上,中室两侧至少各有两个耳室,没有设置肋柱。这两座墓的墓主或为皇帝,或为郡王级高官,等级很高,与之匹配的是大型三室墓。后蜀Aa型的大型三室墓在形制与等级上是与前蜀一致的。后蜀还有Ab型的中型三室墓,对应的是刺史等中级官吏,但前蜀还没有发现这一等级的三室墓,或是后蜀的新发展。

图一三 前蜀永陵墓室平面图
后蜀Ca型墓葬属于大型墓,目前只有宋王赵廷隐墓一例,显示出来自和陵所代表的北源因素的影响。赵廷隐墓只有一个主室,两侧壁各设有一个较大的龛室,须弥座砖石棺床置于主室中部。这些结构与和陵是一致的。以一个主室来代表高等级,不同于后蜀Aa型墓葬以大型三室来反映高等级,这是源自和陵的等级传统。墓室中还绘有人物等壁画,也是延续和陵特征的反映。同时,赵廷隐墓的形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在后壁还设有一个龛室,这与中晚唐蜀地墓葬常见后壁设龛室的做法相同;二是主室和龛室的形状都是长方形,而不是圆形,表明和陵圆形墓的做法已被放弃。后蜀Ca型墓葬虽然等级很高,但与其他几种皆与南源相关的墓葬形制的兴盛程度相比,显示出发展境况的局促。上述两点变化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在南源占据墓葬文化主流的大背景之下,北源因素不得不遭到改塑。
- 三、后蜀墓葬形制的演变与统治集团的蜀地化
后蜀墓葬形制大致代表了三个方面的势力集团或人群。Ca型墓葬代表着孟知祥建国过程中北来的开国功臣集团;A型墓葬代表着后主孟昶执政后期的新政治集团,高级官吏使用Aa型墓,中级官吏使用Ab型墓;B型和Cb型墓葬代表着延续本地中晚唐以来文化传统的下层官吏和平民。B型和Cb型墓葬一直在社会下层稳定发展,变化不大。能够反映后蜀墓葬深刻变化的是Ca型与A型墓葬之间的替变,关联的是后蜀上层统治集团的人员变动与政治、文化取向。
孟知祥建国所依靠的创业勋臣,史称“五节度使”,包括武泰军节度使赵季良、武信军节度使李仁罕、保宁军节度使赵廷隐、宁江军节度使张业、昭武军节度使李肇五人[58]。建国后半年,孟知祥仓促辞世,遗命六大臣顾命,“召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受遗诏辅政”[59]。顾命六大臣中,出自“五节度使”的有三人,另三人为王处回、张公铎、侯弘实。这八人皆从北方入蜀[60],和孟知祥本都是后唐的臣子。他们在后唐灭前蜀过程中进入蜀地,作为战胜者,他们不会继承前蜀的墓葬形制,而是选择后唐中原地区的墓葬形制。孟知祥夫妇和陵就是洛阳地区后唐高等级墓葬形制在蜀地的移植。
后主孟昶即位后,历时十一年方才亲政。其过程就是在逐步排除顾命旧臣对朝廷决策的影响力,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借他人之力除去骄横欺主的李仁罕、李肇。孟昶杀李仁罕,是因为“张公铎、韩继勋、韩保贞、安思谦等皆事后主于藩邸,素怨仁罕,共谮云:‘仁罕有异志’。而廷隐与有隙,亦怂恿之”[61]。后主令韩继勋等与“赵季良、赵廷隐谋”[62]。顾命大臣中有三人参与了谋划。李肇被废,则因为后主“左右以肇倨慢,请加刑”[63]。后主虽对二人愤恨,但还要得到重臣的支持才敢动手。第二阶段,分解或罢除重臣的权力。赵季良本来独判三司,到广政三年(公元940年)时,改为由三人分判三司,“季良判户部,(毋)昭裔判盐铁,(张)业判度支”[64]。广政四年(公元941年),收回三位顾命大臣的节度使兵权,“加卫圣马步都指挥使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枢密使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张公铎检校官,并罢其节度使”[65]。第三阶段,广政九年(公元946年)赵季良去世后,后主加快了对其他旧臣的处置。广政十一年(公元948年)七八月间,后主直接命令壮士击杀张业,逼王处回、赵廷隐交出权力,退出朝政,“自是故将旧臣殆尽,帝始亲政事于朝堂”[66]。至此,后蜀政治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年后,赵廷隐薨,使用的是Ca型墓葬,主室迫于南源因素影响由圆形改塑为长方形,但仍反映着北源因素。在政治形势已经大变的情况下,赵廷隐墓还坚持北源路线,说明在顾命旧臣掌权的后主前期,来自后唐的中原墓葬形制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广政十年以前去世的顾命旧臣有可能会使用圆形墓,或是使用类似赵廷隐墓的形制。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Aa型纪年墓是赠太子太师张虔钊墓。墓主人卒于广政十一年(公元948年)二月二十三日,下葬于当年九月十五日。这段时间非常敏感,正是后主清除顾命旧臣、实现完全亲政的最后阶段。墓葬开建的时间应该早于斗争最激烈的七八月间。Aa型墓是仿前蜀高等级墓葬的大型三室墓。这表明前蜀大型三室墓在后蜀的复现不晚于广政十一年。这种墓葬的出现,显示后主在治国方略上发生重大变化,由建国初期摒弃前蜀,转向到需利用前蜀的资源来执政。
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已从后唐,历经后晋,进入后汉,后蜀与后唐曾经的政治渊源不复存在。晋、汉交替之际,后蜀曾欲北上占领关中,但终归失败。广政十年(公元947年)正月,后晋雄武军节度使何重建以秦、阶、成三州来降;三月,后主派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攻凤州;四月,后晋凤州防御使石奉頵以凤州来降。于是后蜀完全恢复到前蜀时的最大疆域。此后,后蜀与后汉争夺凤翔、长安,欲图关中。至广政十一年(公元948年)底,后蜀退军,放弃争夺[67]。广政十一年是后蜀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北来重臣退隐,北上争夺关中失败,都不断削弱了后蜀与中原的关联性,而不得不重视起蜀地本有的人力和文化资源。
后主杀张业、黜王处回后,需要填补中枢宰臣的空缺,随即“以普丰库使高延昭、茶酒库使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以翰林承旨、尚书左丞李昊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徐光溥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并同平章事”[68]。这四人中除高延昭籍贯不详外,其余3人均是具有蜀地背景的人士,所占比例很高。王昭远、徐光溥直接为蜀人[69];李昊虽生于关中,但前蜀王建时期就已入蜀地为官,任职十余年,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70],与蜀地关系十分密切。李昊、王昭远又最得后主信任,是后主执政后期的核心宰臣。后主还让李昊领衔撰写了《前蜀书》[71],提高对前蜀的重视程度,其中自然包含着深入了解、借鉴的意图。随着后蜀统治集团从核心人员到统治思想的蜀地化,尤其是向前蜀的学习,墓葬文化中前蜀因素必然卷土重来,A型墓便成为后蜀后期墓葬文化的主流。
注释:
[1] a.〔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四《后蜀世家》第802-803页,中华书局,1974年。
b.〔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僣伪列传三》第1823页,中华书局,1976年。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后唐纪六》第9064页,中华书局,1956年。
[3]〔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四十四《唐书·明宗纪》第601页,中华书局,1976年。
[4] a.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第3期。
b.张勋燎、黄伟:《论后蜀和陵的特征及相关问题》,《成都文物》1993年第3期。
[5] 同[4]b。
[6] a.吕学明、吴炎亮:《辽宁朝阳隋唐时期砖构墓葬形制及演变》,《北方文物》2007年第4期。
b.吴炎亮:《试析辽宁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文化因素》,《文物》2013年第6期。
[7] 王乐:《试论京津唐地区隋唐墓葬》,《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
[8] 从目前考古资料看,河北南部仅发现2座唐代圆形墓,均见于邯郸地区,即大名县何弘敬墓和鸡泽县北关唐墓BM2。参见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河北鸡泽县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4年第6期。
[9] 徐殿魁:《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10]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文物》1995年第11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第171、174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2] 《偃师杏园唐墓》第178~180页。
[13] 《偃师杏园唐墓》第181~183页。
[1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后梁高继蟾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
[1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龙盛小区两座小型五代墓葬的清理》,《洛阳考古》2013年第2期。
[16] a.李有成:《代县李克用墓发掘报告》,见《李有成考古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b.杨继东:《极建陵》,《文物世界》2002年第5期。此文“极建陵”为“建极陵”之误。
[17] 曾国富:《略论五代后唐“小康”之局》,《唐都学刊》2008年第1期。
[18] 张荣波:《略论幽州人才向后唐的转移》,《东岳论丛》2014年第5期。
[19]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十八《明宗纪四》第518页,中华书局,1976年。
[20]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后晋孙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第6期。
[21]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晋祠后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2期。
[22]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23]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24]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2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苗北村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26] 赤峰市博物馆、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巴林左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辽代墓葬》,《考古》2016年第3期。
[27] 马凤磊:《后唐德妃伊氏墓志铭释考》,《草原文物》2016年第2期。
[2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双流县文物管理所:《成都双流籍田竹林村五代后蜀双室合葬墓》,见《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此为两座墓葬异穴同坟而葬。其中M1出土石碑上有后蜀广政二年(公元939年)年号,M2出土石碑上有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年号,简报因此视之为后蜀墓葬。但这两座墓均为石室,后龛互通,且出有全套的人物俑、动物俑、神怪俑等。这些特点又与四川宋墓相同(参见陈云洪《试论四川宋墓》,《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颇疑此墓为宋代改葬墓,使用了宋代的形制和随葬品,却保留了后蜀时期的石碑。故暂不将该墓形制列入后蜀时期讨论。
[29]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东郊后蜀张虔钊墓》,《文物》1982年第3期。
[30]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五代后蜀孙汉韶墓》,《文物》1991年第5期。
[31] 简报称通道(本文认为是前室)长1.25米,但从平面图看,前室实际上近方形,故其长度可能是2.25米,1.25米当为笔误所致。
[32] a.年公、黎明:《五代徐铎墓清理记》,《成都文物》1990年第2期。
b.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无缝钢管厂发现五代后蜀墓》,《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
[33] 同[32]。
[34] a.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
b.任锡光:《四川彭山清理后蜀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35] 任锡光:《四川华阳县发现五代后蜀墓》,《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3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年度永陵公园古遗址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
[37] 王毅等:《四川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发掘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6日第8版。
[38] a.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西郊西窑村唐宋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第7期。
b.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郊土坑墓、砖室墓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
[39] 李蜀蕾:《前后蜀墓葬略论》,见《东方博物》第四十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40] 洪剑民:《略谈成都近郊五代至南宋的墓葬形制》,《考古》1959年第1期。
[41] 魏绍菑等:《成都西郊清江路唐宋墓葬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4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北部新区武海·中华名城唐五代墓葬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10),科学出版社,2012年。
[4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唐宋墓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
[44] 同[41]。
[45] 同[43]。
[46] 同[42]。
[4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和平村墓群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11),科学出版社,2013年。
[48] a.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南郊桐梓林村唐代爨公墓发掘》,见《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
b.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南郊唐代爨公墓清理简报》,《文物》2002年第1期。
[4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郊红色村唐代王怀珍墓》,见《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
[50] a.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村唐墓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b.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3期。
[51]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物保管所:《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大道南延线唐宋墓葬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
[5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龙泉驿五代前蜀王宗侃夫妇墓》,《考古》2011年第6期。
[5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管所:《2004年广汉烟堆子遗址晚唐、五代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
[54] 崔世平:《河北因素与唐宋墓葬制度变革初论》,见《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55] 同[49]。
[56]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5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前蜀晋晖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10期。
[58]〔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755-761页,中华书局,1983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5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第9123页,中华书局,1956年。
[60] a.〔宋〕路振:《九国志》卷七第3300-3307页,见《五代史书汇编》(陆),杭州出版社,2004年。
b.《十国春秋》第755~762、767页。
[61] 《十国春秋》第759页。
[62] 《十国春秋》第706页。
[63] 《十国春秋》第761页。
[64] 《十国春秋》第710页。
[65] 《十国春秋》第711页。
[66] 《十国春秋》第716~717页。
[67] 《十国春秋》第714~718页。
[68] 《十国春秋》第716页。
[69] 《十国春秋》第828、775页。
[70] 《十国春秋》第769页。
[71] 《十国春秋》第774页。
-

-

-

-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邮编:100871
邮箱:webmaster@pku.edu.cn
-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
京ICP备05065075号-1
京公网安备 110402430047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