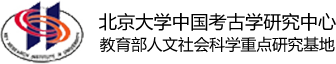优秀论文
返回韦正、方笑天:两汉墓葬陶礼器的变化与原因试探——两汉之变之一端
发布时间:2020年7月17日 来源:纸上考古
摘要:两汉墓葬中随葬的陶礼器有显著差别。西汉至东汉早期的鼎盒壶是庙祭礼器,东汉中后期流行的案盘杯是设奠礼器。两汉随葬陶礼器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二十等爵制在东汉时期的基本废弛。
* 原文刊载于《古代文明》(第14卷),作者及编辑部授权“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刊发,如需引用请据纸版原文。
陶礼器存在两汉之变:从考古学上考虑汉文化的特征,俞伟超先生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自西汉武帝至东汉明、章二帝时期,是汉文化最繁荣的阶段。……埋葬制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依宗法制度安排墓位的族坟墓制度,被家族茔地代替。夫妇并穴而葬变为同穴合葬。随葬品中成组礼器消失,主要是各种日用器皿和象征庄园生活乃至墓主身份的模型明器。从西汉晚期起,为更充分地反映这些内容(包括天道观和历史观),又日益流行壁画墓和画像石墓,用图画来表现之。”[1]俞先生的论述通览全局,高屋建瓴,是后来学者把握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出发点。随着近年来考古材料井喷式的增加,俞先生的基本观点被证明仍然是可靠的。当然,局部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成为了必要。本文拟以汉墓中随葬的陶礼器为中心,对从西汉到东汉陶礼器的显著变化加以讨论。这种变化具有时代性,可以用陶礼器的两汉之变进行概括[2]。
两汉陶礼器之变以往没有充分揭示:对陶礼器的讨论,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俞先生也曾正面加以论述,“在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葬俗一直沿用周礼传统,一般民众的墓葬,几乎都用成组的鼎、敦(或瑚)、壶等礼器随葬。秦人则主要用瓮、罐等日用器皿随葬。但从战国晚期起,凡秦军占领之地,六国遗民原有的传统葬俗,立刻遭到压制,而且要学着秦人的样子,以日用器皿随葬,再也不使用成组的礼器。……但一进入汉代,则从关中到东海之滨,从长城地带到南海之地,从贵族大墓到平民小墓,又重新以成组的礼器随葬。尽管各地出土物的形态有本地特点,但鼎、盛(盒形)、壶、钫是从大墓到小墓的最基本组合。”[3]俞先生对东汉随葬品的讨论集中在模型明器方面,将“模拟庄园面貌的模型明器的发达”称为“西汉中期以后汉文化的主要新特点”之一,俞先生说:“从西汉中期以后,特别是东汉时期,模型明器的种类在逐渐增加,形成了一套象征庄园生活缩影的明器群,从而这种明器的意义已发生变化。”[4]俞先生还说:“墓内随葬品的内容,是墓主在世时期身份地位和财富占有情况的反映,也是墓主亲属希望继续下去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表现。当然,一旦成为葬俗,就成为行为的规范,人们都按照这种规范来放置随葬品。这种葬俗,古人归入‘礼’的范畴。”[5]细揣俞先生文意,仍不能肯定是否以模型明器为礼器。如果模型明器不作为礼器,那么,俞先生对东汉的礼器就没有加以确指。但我们认为随葬模型明器本质上属于葬俗,与“礼”有一定差别。更多的学者是对鼎盒壶为礼器表示支持,但对其消失的原因以及是否有替代品持回避姿态,如刚刚完成答辩、代表最近研究成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云河博士在讨论关中地区东汉—西晋墓葬时说:“关中地区的西汉墓葬中,常以陶质的鼎、盒、壶(钫)组合充当礼器角色,但这一组合在新莽时期逐渐消亡。在东汉墓葬中,陶鼎、陶盒的数量极少,已经不构成组合,依然大量流行的只有陶壶一种。因此,陶壶在东汉时期是否还具有仿铜陶礼器的性质,是值得考虑的。笔者认为,东汉墓葬中仍具有仿铜陶礼器性质的,只有少量遗存的陶鼎,在这里将陶壶归入日用陶器。”[6]李云河博士的观察是可靠的,归纳了现象,但现象发生变化的原因未予深究。从俞伟超到李云河,对汉墓陶礼器的讨论集中在西汉时期,但都没有回答西汉鼎盒壶为代表的礼器消失的原因,或者说,没有回答汉代陶礼器发展演化的走向问题。
案盘杯勺是东汉时期的陶礼器:我们认为,只要丧葬活动中存在礼,就必然有行礼的器物,即所谓礼器。东汉时期丧葬之礼自然是存在的,也就自然存在礼器。东汉现实生活中的丧礼已不可复现,但墓葬中还留下一些证据,那就是棺前的设奠之具,主要包括以案为中心的盘、耳杯、勺等物,还可能包括案附近的壶、罐等。祭奠之礼中,食物集中存放在壶、罐中,被分盛到盘、耳杯之中。这些陶器的组合和陈列方式显然来自于现实中对死者陈尸期间的祭奠活动,是希望死者能像生前一样进行饮食活动。东汉开始的这种祭奠方式后来一直延续,如《搜神后记》卷四“徐玄方女”条说:“晋时,……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醊其丧前……。”[7]两晋时这类陶器被涂成有别于其他随葬陶器的红色,也是沿袭了东汉时期并被强调而已。[8]因此,墓葬之中、棺椁之前以案为中心的设奠之具就是东汉墓葬中的礼器。礼始诸饮食,与饮食相关的器物在东汉以后成为最核心的礼器,似乎又回到了礼的本来意义上去了。
以往学者没有将案盘杯勺明确认定为陶礼器:在墓室中设奠早有学者言及,如黄晓芬在讨论满城汉墓时说:“……前室岩洞内也特别造设有瓦顶建筑物,其间整齐配列和陈设有各种供献祭祀品。在此还发现有铭记‘中山祠祀’的封泥,表明随葬品当中有不少为祭祀中山王而制作的专用品。至此,在地下玄室棺室前方的特定空间内陈列祭祀品,实施并展开对墓主本人进行的供献祭祀活动已走向定型。……东汉以后,汉墓随葬品的组成及在室内各空间的配置形式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玄室内的构造与随葬品的空间配置特点等,都突出表现出了祭祀空间之重要。祭祀空间位于棺室前方,又往往占据整个玄室内的最高位置。祭祀前堂内一侧多设置有高0.20米左右的砖(石)台,……这种砖石砌筑的祭台或石制几案等都应属室内配套制作的祭坛设施。灵宝县张湾M3的随葬品保存完好,随葬品组成及配置亦值得注目。这里在砖砌玄室的祭祀前堂和后室棺位的前侧,分别陈设、配置有陶案、杯、盘等实物供献祭祀品,其周围按一定方位摆放有陶制明器的仓、灶、井、厕等。”[9]黄晓芬的论述是客观的,但黄晓芬没有用礼器这个概念来概括棺前设奠的器物,从而未能进一步从礼器变化的角度讨论两汉之变。
墓葬形制的改变不是两汉陶礼器之变的主要原因:上文黄晓芬所引述的例证是西汉的崖洞墓和东汉的砖室墓,其共同特点是都有可以供人自由移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能够布置出墓主生前的起居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与墓主最密切相关的是饮食。《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对一号汉墓中室中部帷帐前的情况叙述道:“中区东部的随葬品主要是铜器,其中有鼎、镬、釜、甗等食器和炊器;锺、罍、链子壶等酒器;鋗、盆、灯、薰炉等日常生活用具。”[10]对漆器出土状况叙述道:“漆器出土于后室和中室,数量相当多,但都已残朽……。”[11]检查一号墓中室器物分布图,在中部帷帐前有漆案和漆耳杯。综合上述情况,可见满城一号汉墓像以灵宝县张湾M3为代表的东汉砖室墓一样都有专门的饮食景象的模拟。(图一)那么,是否因为墓室中出现可自由移动的空间才导致了饮食器的普遍设置呢?应该不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是典型的木椁墓,发掘报告说:“北边箱(引者注:即头厢)象征死者生前的生活场面,四壁张挂着丝织的帷幔,底部铺以竹席。北边箱的中部,陈设着漆钫、漆勺和陶壶等酒器,以及放置在漆案上的漆卮、漆耳杯和盛有食品的小漆盘等宴享用品。北边箱的西部,陈设着漆屏风、漆几、绣枕、熏囊和两套梳妆漆奁等起居用具。北边箱的东部,有着衣女俑、着衣歌舞俑和彩绘乐俑。另外,还出土了一件夹袍、两双鞋,以及陶熏炉、竹熏罩、小竹扇和木杖等物。这些正是死者生前多蓄奴婢,过着‘极滋味声色之乐’的糜烂生活的写照。”[12]因此,我们认为棺前设奠是早已有之的观念,但其普及则与横穴式墓的逐渐流行有关。传统的木椁墓墓室通常较为低矮,不允许充分按照现实场景布置,只有横穴墓才提供了供人自由活动的空间,并且使墓葬在模仿地面建筑和现实生活方面都大为便利。但墓葬形制的改变只能为棺前设奠提供便利,并不能解释鼎盒壶的消失,不能解释何以墓葬中的礼器从鼎盒壶变化为以案为主的一套饮食器。


图一 满城一号汉墓中室、灵宝张湾M3平面图
(1.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图一六,文物出版社,1980年 2. 引自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第11期)
两汉陶礼器的变化源于宗庙之祭变为饮食之奠:崖洞墓和砖室墓中所布置的起居场景兼具现实模拟和祭奠两种性质。西汉时期的这个场景中,鼎盒壶既不是最主要的器物,也没有占据最显眼的位置,如洛阳西汉张就墓鼎盒有两套,出土位置紧邻,但都在耳室之中。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基本也是这样。因此,西汉时期的鼎盒壶组合不是直接来自于起居场所之中,需要另作考虑。
实际上,鼎盒壶也是以饮食之奠为中心,但这个组合所代表的是宗庙之祭,与案为中心的饮食之奠有很大差别。鼎盒壶消失的根本原因是宗庙之祭的不再普遍实行,是两汉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所致。饮食之奠在宗庙之祭中也已经存在,但并不占有特殊地位,在宗庙祭礼废弛后,饮食之奠就突出了。
鼎盒壶与宗庙中进行的丧礼用器相似:鼎盒壶本是三种不同性质的器物,分别是炊煮、盛放、储藏用器,这是按照考古类型学原则从随葬品中挑选出来的数量最多的三种器物,但将它们当作礼器看待仍然差强合适,这不仅在于它们频繁出现且经常在一起,还因为它们与庙堂之祭的礼器相近。高崇文先生撰有《论西汉时期的祭奠之礼》一文,经研究后指出:“从考古发现看,西汉前期的墓葬多沿用先秦的丧葬礼仪,西汉后期则发生了大的变化,表明新的汉代葬制已彻底代替先秦古制,进入到新的‘汉制’阶段。”[13]高崇文先生在这句话的后半截所说的汉制,可以看作是接着俞伟超先生的话而讲的,帝王列侯等人的丧葬在西汉时期表现出连贯性,显得相当保守,还是多沿用先秦丧葬礼仪。因此,《三礼》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用于我们的研究。西汉像先秦时期一样,在葬日前两天,将棺柩迁至祖庙,是谓“迁祖奠”;葬日前一天,进行准备离开祖庙的祖奠之仪。这两日祭奠的“所设之物如大敛奠,除有两甒醴酒、两豆脯醢外,还有三鼎之实而载之三俎的豕、鱼、腊”。[14]葬日设大遣奠,《仪礼·既夕礼》载:“厥明,陈五鼎于门外,……四豆,……四笾,……醴酒。陈器。”因为是葬前的最后一次祭奠,所以用五鼎,示礼加一等。高崇文说:“以上是《士丧礼》、《既夕礼》所记载的自始死至埋葬期间的整个祭奠仪程,是士一级的祭奠仪式,其他级别的贵族也有同样的祭奠仪式,只是所用礼的隆杀有异,尤其表现在所用牢鼎的等级上。”[15]在丧葬仪式过程中,鼎无疑是礼器的中心。是否用鼎,关乎是否为先秦之制。东汉普通墓葬几乎不用鼎,表明先秦丧葬已经消亡,新礼诞生。西汉前期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道中的陪葬墓、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马王堆1号墓、3号墓等墓葬都有成组的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道中陪葬墓的五鼎在墓主脚端一字排开,对先秦古礼的遵守似乎更严格。西汉后期墓葬中多有铜鼎、陶鼎发现,说明先秦古礼仍有约束力。早先丧葬礼仪中用于盛放食物的豆、笾,逐渐演变成了不带柄的盒。至于鼎盒壶中的壶似乎也可与盛酒的甒相应。因此,鼎盒壶组合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将庙祭的炊煮、饮食、储藏之器移到墓葬之中,只是由于木椁墓空间上的限制,很少能够按照实际使用情况陈列而已。
先秦西汉丧礼用器是全部庙堂礼器的一部分:从《仪礼》等文献可知,丧葬礼仪用器很多,鼎盒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钱玄说先秦时期“迎送宾客、燕饮、祭祀、射礼均奏乐。”[16]可知丧礼无乐。如果将墓葬中经常出土的编钟编磬等乐器也一并加以考虑,那么丧葬礼仪用器也只是整个庙堂礼器的一部分。将鼎盒壶这个组合抽离出来便利了今天对器物形态的考察,但几乎堙没了先秦西汉时期墓葬随葬品是按照庙堂礼器而安排的事实。因此,只有进行长时段的观察,并且对身份不同的墓主人加以区分,才能对鼎盒壶的器物组合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各种青铜礼器与乐器共出的墓葬,但最具有代表性的当为曾侯乙墓。曾侯乙墓中室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庙堂之祭”的器物组合,“南部全是青铜礼器,出土时这些青铜礼器成组成排,放置得井然有序。紧贴中室南壁,置束腰大平底鼎两排九件(一排六件,一排三件),其中一件上又置一匕。贴近束腰大平底鼎置八件簋、九件小鬲和十件小的鼎形器,其南置五件盖鼎,每件盖上置鼎钩两件,排得整整齐齐,很有秩序。西南(角)放置一件提链鼎和两件陶缶。靠近陶缶有四件铜盥缶……。中部,靠近束腰平底鼎和盖鼎的地方,并排放置两件大铜鼎,……靠近大鼎和盥缶,还有四件簠和一件甗,再往南即是编钟的南架。编钟架呈曲尺形紧靠中室西壁及南部偏中,编磬靠近北壁,钟、磬组成三面环绕的形式。在空缺的一面,即贴近中室东壁,放置尊盘、过滤器、鉴缶、联禁大壶及建鼓。在它们与钟磬组成的空间内放置瑟、笙、排箫、篪等乐器以及食具箱、酒具箱、耳杯、俎等漆木器。”[17]在编钟等乐器之外,中室主要是青铜器物,其中鼎、簋、鬲、簠、甗、缶等物当是礼器。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虽然不是墓葬,但颇能说明问题,马坑、乐器坑外,还有大量的青铜礼器坑,主要器物为鼎、簋、壶、鬲。虽然器物类型的复杂程度和数量都不及曾侯乙墓,但这些青铜器和乐器更能集中反映庙堂礼器的实质部分。西汉诸侯王、列侯墓葬中经常发现编钟编磬和青铜礼器,这正是沿袭了先秦礼仪。列侯以下人物,虽然没有资格使用编钟编磬等乐器,在经济上也许还无法承受使用青铜礼器的负担,但仍然使用了仿铜陶礼器,这可以解释鼎盒壶为什么在西汉长期存在。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曾侯乙墓中室的这个庙堂器物群中,有两件壶形陶缶(C.192、C.193)、漆木质的豆、耳杯、木勺、筒形杯、豆形杯、卮杯等,这些才可能是曾侯乙实际使用的器物。青铜器是可供陈列,而几乎无法使用的,如中室也随葬了青铜豆,两件浅盘豆的高度均为21.6厘米,带盖豆的高度为26.4厘米,高度是漆木豆的一倍左右,显然不是真正的实用器皿。两件壶形陶缶之外,曾侯乙墓出土陶器极少,可见陶器也不是曾侯乙这个身份的人日常使用的器皿,漆器才是当时的实用器皿。东汉陶案为主的饮食礼器组合所代替的应该也是漆器。
西汉王侯拥有宗庙:能够使用宗庙礼器的前提是墓主拥有宗庙。西汉时期不仅诸侯王,列侯也可以有自己的宗庙。王鹤鸣、王澄检出了相关资料,值得转引:“(西汉)诸侯、列侯也有自己的宗庙制度。列侯的宗庙,见于金日磾的事例。金日磾在宣帝时受封为侯,传子赏,赏无后,金当继承金赏。金日磾侄安上,受封都成侯,传子常,常无后,金钦继承金安上。……金钦曾鼓动金当为其父祖立庙,而不祭其从祖金赏,‘当名为以孙继祖也,自当为父、祖立庙。赏故国君,使大夫主其祭。’金钦的做法遭到甄邯的弹劾,认为:‘赏见嗣日磾,后成为君,持大宗重,则礼所谓‘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绝者也。……当即如其言,则钦亦欲为父明立庙而不入夷侯常庙矣。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裁定金钦诣诏狱,金钦自杀。由这个事件可知,列侯有庙祀;大宗不可绝嗣,金当、金钦既为他人大宗之后,不可以再祭祀亲生的祖、父;金钦所犯之罪是‘大不敬’。由此可知,诸侯与列侯宗庙的依据均是先秦宗庙礼制。”[18]那么,继续采用先秦的宗庙礼器也顺理成章。不仅列侯,西汉时期关内侯至七级的公大夫(文景以后为九级的五大夫)也有很高的地位。《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在汉五年颁布诏书说:“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朱绍侯先生说:“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刘邦以后的汉政府虽然再也没有颁布过这样的诏令,但以后的汉政府也并没有废除这个诏令。从刘邦诏令中……的严厉语气来考察,汉五年的诏令是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的。仅这一大批七大夫以上的食邑者,在汉初三四十年内是不会消失的……。”[19]这些食邑者多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军人,刘邦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优待,而且他们在汉朝建立后多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集政治、经济地位与爵位于一体的这些人不可能不享受礼制上的待遇,而且还必须与他人有所区别。尽管列侯以下人物的礼制待遇史书有缺,但如同先秦公卿大夫士或公侯伯子男通过服章名物加以区别一样,西汉恐怕还得借助这个手段。在服章名物之中,鼎仍然最能代表身份。关内侯以下人物尽管不能建立宗庙,也不能演奏钟磬,但他们当有类似宗庙式的“家庙”,能在其中进行礼仪活动,并主要通过鼎来标榜自己的身份。
西汉时期高等爵位仍然很有价值:已有研究表明,由于战争的减少和政府卖爵,文景之后二十等爵制受到较大冲击,但趋于轻滥的是其中的低等爵位,也就是第八级公乘以下的民爵,第九级五大夫以上的高等爵位仍然受到严格控制,可以举出的代表性例证是武帝时将爵位赐予后宫的嫔妃。《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载:“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倢伃视上卿,比列侯(二十级爵)。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十九级爵)。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十六级爵)。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十五级爵)。……长史视六百石,比五大夫(九级爵)。少史视四百石,比公乘(八级爵)。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史、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字、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20]朱绍侯先生说:“……少使以上都有官、爵对比关系,而五官以下仅有官秩视若干石,而没有相应的爵位对比关系。这是因为少使比公乘,已经比到民爵的最高级,五官以后如果再与爵位对比,就进入毫无特权的民爵级别,因此也就再没必要与爵位挂钩了。”这个认识是很有见地的。但朱先生接着说:“把军功爵赐给后宫妃嫔,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对军功爵制的重视,实际是对军功爵制的最大讽刺与亵渎,说明军功爵已变成了后宫的点缀品,这是军功爵制在西汉的中后期日趋轻滥的又一种表现。”[21]这个说法难以完全赞同,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为何授予妃嫔爵位加以理解,那就是这个时期的二十等爵已经具有阎步克先生所提出的“品位”的意义。阎步克说:“爵级是一种‘品位分等’的制度。……二十等爵不是官阶制,可它作为一种政治等级,在秦汉帝国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十等爵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它使平民得以通过军功获得爵禄,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在另一方面,二十等爵又是一种身份性、品位性的制度。‘爵’的形式,依然体现了早期社会、贵族政治的深厚影响。刘邦下令保障拥有军爵者的政治社会特权,这时他还有‘爵在人君’的说法,就充分显示了‘爵’浓厚的传统意味。对汉初的军功阶层,军爵是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基本尺度。换言之,我们看到‘爵’的背后是一个阶层。而且同时在王子侯和外戚恩泽侯的制度下,皇族和外戚都以‘爵’来确定身份,在汉帝国中这些人具有无可置疑的贵族身份。就是向编户赐爵的做法,也具有安排和确认社会身份的意义,这一点西嶋定生已有很好的考察。进而对于官僚来说,获得了爵级,就等于拿到了贵族俱乐部的会员卡。秦汉时代依附于‘爵’的众多权益,远远大于后世,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近年《二年律令》中新的发现,例如依爵级而占有田宅的规定,以及其他特权,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点。”[22]附着在秦汉二十等爵上的好处是很多且具体的,也没有因为西汉历史进入中后期而减损太多,并且在汉武帝时发展成为规范不同人物身份的一个统一标准,这个标准与官位不同,只能保持爵位的传统色彩,向礼仪待遇方面倾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标志庙堂礼器的鼎盒壶组合在整个西汉时期的墓葬中长盛不衰,但一进入二十等爵名存实亡的东汉就迅速销声匿迹了。
以鼎为中心的陶礼器组合继续存在于东汉诸侯王一级墓葬中:在确认了西汉墓葬中的鼎盒壶组合来自于庙堂礼器、东汉墓葬中的案盘杯勺组合来自于丧葬设奠之后,下面试对鼎盒壶组合消失的原因加以探讨。我们认为,鼎盒壶组合的消失与二十等爵制的衰微有直接关系。在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说明鼎盒壶的消失问题与东汉诸侯王一级人物无关,鼎仍然存在于这些人物的墓葬中,也就是说这些人物依然沿用者先秦以来的庙堂礼器。东汉诸侯王陵中发现陶鼎的有扬州甘泉山二号墓、临淄金岭镇1号墓、定县北庄1号墓、济宁普育小学东汉墓,其中临淄金岭镇1号墓出土陶鼎9件,高度从约26到35厘米,是否为列鼎不详,但可知鼎具有明确的礼仪性质。临淄金岭镇1号墓年代被推定为公元70年,定县北庄一号墓的年代被推定为公元90年,扬州甘泉山二号墓年代有学者认为不是东汉早期而是东汉晚期[23],在疑似曹操墓的安阳西高穴大墓、安徽当涂天子坟[24]也出土成组的陶鼎(图二),这些墓葬在时代上连为一线,说明东汉乃至曹魏时期诸侯王一级墓葬仍然延续先秦西汉时期的列鼎之制。这些墓葬中的陶鼎只能是现实生活中庙堂用鼎的再现。

图二 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陶鼎
(引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曹操高陵》,图六三-六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东汉时期二十等爵名存实亡:东汉时期二十等爵虽然存在,但列侯以下爵位的价值与西汉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续汉书·百官志》所列举的东汉时期爵级只有王、侯、关内侯三种,而不像《汉书·百官公卿表》那样将二十等爵全部列出,可见从西汉到东汉,爵位制度已经严重退化,列侯以下人物的政治经济特权既不见明文规定,礼制上的特殊地位大概也无从谈起。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说:“东汉时期,世家豪族地主阶层已经形成,他们通过察举、征辟和任子制度,完全垄断了政治特权,布衣之士,包括一般地主在内,已很难进入政治舞台,完全用不着以‘赐吏爵’去扶植新的权贵了。所以东汉时‘赐吏爵’一次也没有,可见已经废除。至于‘赐民爵’成了一种更廉价的点缀品。……于是爵制名存实亡。正如王粲《爵论》所说:‘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赐而法也。今爵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也不惧,赐之,民也不喜,是设空文书而无用也。’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汉是赐爵最多的朝代,但人们竟不知赐爵的用意何在,甚至连熟悉官事的一些文吏也弄不清楚‘赐民爵八级何法’。可见军功爵制在东汉只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但也要说明一点,所谓军功爵在东汉已经失去实际意义,乃是指十八级以下的爵位,至于最高两级,即关内侯、列侯,则仍以分封制的残余形式被保留下来。”[25]实际上,列侯在东汉的地位也在下降,《续汉书·百官制》说:“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赐位朝侯,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次大夫。其余以胏附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亦随时见会,位在博士、议郎下。”[26]东汉列侯地少力微,与朝廷官员相较,类比的级别降低,所拥有的特权主要只是能够参加朝会、祠祀、墓祭等礼仪活动。上文指出东汉诸侯王一级人物的墓葬中仍然用鼎,但在疑为东汉时期的列侯墓葬中,都没有发现陶鼎。这从《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中似乎也能看出一些端倪。《续汉书·百官志》叙述诸侯王时云“礼乐长。本注曰:主乐人。卫士长。本注曰:主卫士。……祠祀长。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叙述列侯时云:“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中兴以来,食邑千户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不设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马、门大夫。”[27]叙述关内侯时云:“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细绎上述引文,列侯、关内侯都没有专门的礼乐属官,也应没有独立的宗庙,所有者大概是祠堂之属,自然没有庙祭的列鼎。[28]更不用说列侯、关内侯以下的人物了。
墓葬中的礼器是现实礼仪的再现:综上,墓葬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折射,墓葬中所发生的变化只能是现实社会发生变化的结果。丧礼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仪之一,墓葬不能不对丧礼有所反映,但除礼仪场所和气氛非常特殊外,从三礼等文献来看,丧礼所使用的器具即礼器的主要种类与其他礼仪活动大致相似,这是庙堂礼器得以出现在先秦西汉墓葬中的原因之所在。先秦礼仪活动的依据是贵族身份,秦汉二十等爵延续了这一贵族特性,但东汉从光武帝开始就高度强调吏治,“职位”的重要性迅速超过爵位所代表的“品位”,加上明帝开始对包括列侯在内爵位授予的吝啬和权益的削夺,终于使二十等爵的有效性在东汉早期基本终止了,庙堂之祭只限于诸侯王以上的最高级贵族了,这就决定了带有先秦庙堂礼器特点的鼎盒壶组合在诸侯王以下人物的墓葬中也不得不在东汉早期前后消亡了。本包括在庙堂礼器之中、但被其他重器掩盖,且损之不能再损的饮食之器遂成为礼器而走到核心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将西汉归为上古时代,将东汉看作中国中古时代的开始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注释:
[1] 俞伟超:《秦汉考古学文化的历史特征》,载氏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2] 实际上西汉中晚——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这两个阶段的变化更能反映西汉、东汉的时代差异,但为行文方便,正文中使用了简洁的表达方式。
[3]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载氏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4]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载氏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5]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载氏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6] 李云河:《关中地区东汉至北周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论文,2018年5月,第40页。
[7] (晋)陶潜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中华书局,1981年,第24页。
[8] 两晋时期这类墓葬发现甚多,在两晋首都今天洛阳和南京有很多发现,东汉这类墓葬,如淅川县香花镇杨河组汉墓M1、M2,见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北京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淅川县香花镇杨河组的四座汉墓》,《南方文物》2011年2期。
[9]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214、215页。
[10]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11]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44页。
[12]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35页。.
[13] 高崇文:《论西汉时期的祭奠之礼》,载氏著:《古礼足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4页。
[14] 高崇文:《论西汉时期的祭奠之礼》,载氏著:《古礼足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5页。
[15] 高崇文:《论西汉时期的祭奠之礼》,载氏著:《古礼足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6页。
[16] 钱玄:《三礼通论》,页553,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7]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页60、64,文物出版社,1989年。
[18] 王鹤鸣、王澄:《中国祠堂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1、72页。
[19] 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75页。
[20]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935页。括号中爵级系朱绍侯先生所加。
[21] 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0、121页。
[22] 阎步克:《官阶与服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4页。
[23] 汪俊明:《扬州甘泉山二号墓年代献疑》,《东南文化》2012年2期。
[2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当涂天子坟出土九鼎八簋,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叶润清研究员惠示。
[25]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齐鲁书社,1985年,第445页。
[26] (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续汉书·百官志(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630页。
[27](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续汉书·百官志(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9—3631页。
[28] 汉魏洛阳城西白马寺汉墓有墓园,园中有寝殿类建筑,《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将此墓认定为列侯一级墓葬,这个认定可能有误。此墓不仅古代有皇女冢的传说,而且墓园建筑布局近似西汉帝陵,建筑规模大,类似宫殿,可能为寝殿,但是身份高于列侯者的墓葬。
-

-

-

-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邮编:100871
邮箱:webmaster@pku.edu.cn
-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
京ICP备05065075号-1
京公网安备 110402430047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