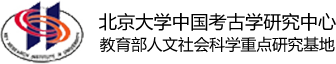优秀论文
返回刘未: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
发布时间:2021年9月10日 信息来源:纸上考古
刘 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作者授权“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刊发,如需引用请据纸版原文。
一
学界以往关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讨论[1],主要从学科整体出发加以比较,着眼时代侧重于先秦,也更倾向主张考古学对历史学的积极意义。这些讨论虽然注意到考古与文献材料在生成方式、涵盖范围等方面的差异,但更多的还是强调两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互补作用,强调文献所见历史背景对于考古材料解释的参照作用。一言以蔽之,更倾向于将考古与文献材料加以结合而非对立。
如此理念正与夏鼐、王仲殊对考古学的经典界定相呼应:“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 “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时代以外,还应该包括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历史时代不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还包括秦汉及其以后各代;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对的。当然,历史越古老,文字记载越少,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显著。”[2]以上表述所隐含的价值判断是:考古学与历史学具有共同的目标,但在内容和时段方面互为补充;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在历史研究方面具有等效的价值;所以,在两个学科之间,文献越丰富的时段考古学较历史学的作用越小;而在考古学科内部,时段越早的断代考古作用越大。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在海外学人外部观察的批评及本土学科独立意识的激发下,中国考古学“补史”的意义反而遭受重点批判。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将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特点称之为“编史倾向”(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具体表现为:考古学家把首要任务看作是为狭义历史学问题提供结论;考古研究完全关注从传统历史文献中提出的问题;考古报告中常常努力但不可信地将考古发现与已知的历史事件、人物或族群相联系[3]。张海则称之为“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突出表现是在考古学研究中以历史文献为线索、以考古为实证的证史主义倾向,以及借助文献史学研究构建考古学的解释理论[4]。其他学者如赵辉[5]和徐坚[6],也同时从类似角度进行批判分析。
无疑,这些批评声音使得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关系、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需要重新予以思考。但迄今为止,学界意见仍不统一。在2006年出版的两部周代研究英文论著中,李峰[7]和罗泰[8]给出了相似的提议,他们更强调考古与文献作为不同信息系统的相对独立性,进而强调考古学与历史学有别的相对独立性。罗泰在后来的访谈中将基于如此理念的研究方法称之为“分行合击”,主张采用适当的方法平行研究,分别处理考古和文献材料,最后再把两者相结合得出结论[9]。不过,在2018年出版的夏代研究中文论著中,孙庆伟则给出了大相径庭的方案,提倡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要求带着具体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并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10]。陈淳随即就此提出异议,赞同李峰、罗泰所论,认为将考古与文献两类材料缺乏审视地结合会产生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应该是信息的互补关系,而非对具体时间、事件和人物的印证关系[11]。
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之间关系的争议并非中国考古学所独有,按照罗泰的说法,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考古学中都具有共性,只是因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丰富及其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而使问题被放大[12]。那么,西方考古学(尤其是历史考古学)在这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可以为中国考古学(不限于先秦考古学)提供怎样的参照?在学界以往的讨论中很少涉及,而这正是本文希望加以简要回顾并评论的问题。
二
实际上,与夏鼐、王仲殊相似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价值判断也是西方学界的传统认识。古典学家芬利(Moses Finley)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不言而喻,考古学对历史的潜在贡献大体上与现有书面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成反比。”[13]莫里斯(Ian Morris)更将其比喻为“零和游戏”(zero-sum game)[14]。
当然,同样在古典学领域,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后来就认为这样的看法存在明显的缺陷:“我们不应该期望文物和文献之间有任何等价性,因为它们是在过去的活动中以非常不同的‘层次’和‘尺度’创造出来的。因此,书面资料和物质遗存之间的巨大一致性暗示了循环论证。”[15]也就是说,如果秉持考古与文献同质互补思维,当文献材料占优势地位时,考古材料最多被当做历史研究的次要证据来予以运用,考古学研究也就难以摆脱历史学框架,被视为同义成果的异化表现形式,考古学就成了“历史学的婢女”。
不过,总体说来,传统的理念在文化历史考古学流派下兼容性尚好,只是当考古学有所发展,理论范式向前推进,尤其是过程主义考古学(新考古学)的影响波及历史考古学领域时,不满的声音才集中迸发出来,出现了一股反文献材料、反历史学的潮流。就如新考古学的代表性人物克拉克(David L. Clarke)率先指出的那样:“历史叙事作为考古结果的载体,其危险性在于,它以其流畅的覆盖面和明显的终结性取悦于人,而它所依据的资料却永远不全面,永远只能支持一种解释,并建立在复杂的可能性之上。考古资料不是历史资料,所以考古学不是历史学。”[16]
进一步以中世纪考古学为例:当1982年中世纪考古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拉茨(Philip Rahtz)在“新中世纪考古学”的旗帜下明确宣称,这是一门具有自身理论基础的学科,可以独立于文献证据,得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17]。索耶(Peter H. Sawyer)同时提出了相似意见,认为考古学家应该专注于自身,抵制大量使用文献或语言证据的诱惑,谨防将结论建立于文献证据之上。如果考古证据符合假定的历史情况,结果显然是循环的[18]。巴恩斯(Gina L. Barnes)则指出,考古与文献材料相结合,如果只是用来说明从文献已知的东西,便将导致误用和滥用[19]。她将这种先入为主的结合比作“配对游戏”(matching game)。而里斯(Richard Reece)的看法更为激进,他认为:“当物质材料和文字材料都存在的时候,关于过去的研究显然要涵盖两者,但每个分支都是不同的、独立的研究,具有自身的资料、方法、目标和结论。当两个分支学科各自发展其研究时,对过去的研究将会受益,因这样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具有两种独立的资料来源。而如果两个可以提供独立证据的学科以一种环环相扣的形式参与循环论证,各自参照另一学科来说明问题,对过去的研究将会失败。”[20]
尽管伴随着批评的声音[21],这种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考古学与历史学近乎对立起来的态度差不多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1990年奥斯汀(David Austin)文章中的抱怨之声[22]——几乎所有中世纪考古研究论著所处理的问题与理念都来自历史学而非考古学自身——可以作为这个阶段考古学家态度的集中总结。
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23],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语境(context)观的兴起,强调考古学独立性之余也注重向历史学吸取经验,提出需要重新把握和历史学的传统纽带[24]。而从更广的学术背景来考察,这又可以看作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潮流的一个缩影。以绍尔(Eberhard W. Sauer)的观点为例:考古学与历史学无论从材料还是路径方面都各具特点,不必追求孰高孰低,所以“考古学家没理由在其偏爱的研究方法对重建人类历史的贡献价值方面产生自卑感,没必要、也没理由去争辩历史文献必然不如自己用物质证据的解释更客观。”[25]
三
不过,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一旦试图将考古与文献材料都纳为自己的研究证据时,就面临着“越界”的风险。按照罗泰的表述:“对考古非常精通的学者随便处理他们并不熟悉的文献的时候,会让研究文献的专家觉得他们很无知;反过来,我们考古学家对那些纯历史学家或者说纯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使用考古材料的方式也很不满。”[26]斯诺德格拉斯也提示历史学家:“考古学证据特别容易引起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有时考古学家会对他自己的发现本身产生误解;更经常的是会对自己和别人的发现的意义产生误解;同样经常的是历史学家会对从一般考古资料或从某一特别发现中可允许的推论范围产生误解。”[27]这意味着在经常需要兼顾考古与文献材料的历史考古学中,更有必要对两类材料的属性具有清晰的认识。
那么,如何具体看待考古与文献材料各自的特点以及评估由此对研究所构成的潜在影响?
问题之一:文献材料是主观的,考古材料是客观的?
费灵(Günter P. Fehring)在表述中世纪考古学的定义与理念时提出了比较传统的看法:文本通常是有意识的主观交流媒介,与考古学家所使用的客观遗存相对立。如果说文献材料保存了社会生活规范,考古材料则往往反映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现实[28]。但斯诺德格拉斯就对考古材料所谓的客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考古现象虽然是客观的,但经过报道的考古资料实际是一种当代人观察记录形成的文本,与历史文献具有类似的性质,所以一份发掘报告就是一段书面历史[29]。可见,无论是形成于过去的文献材料还是呈现于当今的考古材料,都可视为人们出于某种目的所制造的文本,其生成的过程、书写的话语,有必要在具体情境中予以批判分析。
问题之二:文献材料更多反映精英世界,考古材料更多反映民众世界?
富纳里(Pedro Paulo A. Funari)等在检讨历史考古学理论方法时指出:通常认为文献由精英阶层所掌握,虽然新文化史扩展了文献的范围,仍然普遍相信考古学有能力颠覆文献的主导叙事,但为此考古学家必须考虑到书面证据和物质证据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在文献中缺少记载的民众阶层,他们的物质遗存也难以捉摸。所以,“如果历史考古学要讽刺经常体现于文献材料中关于权力和身份的主导叙事,那么就必须发展出另一种寻找边缘群体和被统治群体的考古学路径。”[30]就此,约翰逊(Matthew H. Johnson)同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31]。可以说,随着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兴起,历史学早已摆脱了“帝王将相”的局限,发生“眼光向下”的学术转向。而对于考古学来说,一来仍对那些与文献记载密切相关、利于建构宏大叙事的国家史迹、精英遗存抱有浓厚兴趣,二来对文献中失语者所留下同样无声的物质材料如何有效解读还面临挑战。仅仅坐拥材料“优势”对考古学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四
综上所述,中国学界围绕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关系、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不同意见的发展历程在西方学界也曾经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考古学各领域的相关讨论都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指向了一种新趋向:随着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物质文化证据,以及考古学家试图运用文本分析策略来阅读考古材料,这两个学科已经进入了越来越强调跨学科合作及重新考虑学科边界含义的时期[32]。于是,在材料的综合运用方面,倾向于不再僵化地强调考古与文献材料之间的区别,而是提倡取向的多样性[33],既需要对考古材料进行文本分析,也需要注重文献材料的物质性,两者都需要置身于特定的语境之中予以理解[34]。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基于文字证据的多样性及考古与文献材料关系的复杂性,打破传统认识,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也可以从学科夹缝之间的尴尬处境中解脱出来。一方面,通过排除考古与文献同义性的威胁,抵消历史学随着研究时代变晚文献数量增加而无形中趋于扩大的历史解释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利用晚期时段更为充分的考古与文献资料获知历史表现的复杂性,反思早期时段因资料限制而呈现的历史面貌残缺及其对考古与文献相结合解释历史可能造成的影响。
如此一来,考古与文献材料之间的关系就从强调性质相同的一致性互补,转变为强调性质相异的多样性互动。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考古学不同断代之间也不再因文献丰富程度之别而有彼此轻重之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正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应有之义。
附记:本文内容曾于2020年9月1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与考古学对话活动中报告讨论。
注释:
[1] K. C. Chang,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Vol. 13, No. 2, 1981, pp. 156-169. 张光直著,陈星灿译:《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等。
[2]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页。
[3]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Vol. 67, No. 257, 1993, pp. 845, 847. 陈淳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4] 张海:《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华夏考古》2011年第4期。
[5] 赵辉:《怎样考察学术史》,《考古学研究》(九),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832-833页。
[6] 徐坚:《作为南越国考古学起点的龟岗和猫儿岗:发现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学刊》第9卷第1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2页。
[7] Li Feng, 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 16. 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10、18-19页。
[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UCLA, 2006, p. 13. 吴长青等译:《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9] 孟繁之编:《罗泰访谈录:学术•考古•人生》,太原,三晋出版社,2019年,第31页。
[10] 孙庆伟著:《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13-14页。
[11] 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12]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Vol. 67, No. 257, 1993, 847. 陈淳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13] Moses I. Finley,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Daedalus , Vol. 100, No. 1, 1971, pp. 174-175.
[14] Ian Morris, “Archaeologies of Greece”, in Ian Morris ed., Classical Greece: Ancient Histories and Modern Archaeolo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0.
[15] Anders Andrén, Between Artifacts and Text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1998, p. 23.
[16] David L. Clarke, Analytical Archaeology, 2nd e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8, p. 11. First published in 1968.
[17] Philip Rahtz, “New Approaches to Medieval Archaeology”, in David A. Hinton ed., 25 Years of Medieval Archaeology, Sheffield: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1983, p. 13.
[18] Peter H. Sawyer, “English Archaeology before the Conquest: A Historians’ View”, in David A. Hinton ed., 25 Years of Medieval Archaeology, Sheffield: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1983, pp. 46-47.
[19] Gina L. Barnes, “Mimaki and the Matching Game”, Archaeological Review from Cambridge, Vol.3, No. 2, 1984, p. 37.
[20] Richard Reece, “Sequence is All: Or Archaeology in a Historical Period”, Scottish Archaeological Forum, Vol. 3, No. 2, 1984, pp. 113-115.
[21] Stephen T. Driscoll, “The New Medieval Archaeology: Theory vs. History”, Scottish Archaeological Review, Vol. 3, No. 2, 1984, pp.104-109. Kathleen Biddick, “Decolonizing the English Past: Readings in Medieval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32, No. 1, 1993, pp. 1- 23.
[22] David Austin, “The ‘Proper Study’ of Medieval Archaeology”, in David Austin and Leslie Alcock, eds., From the Baltic to the Black Sea: Studies in Medieval Archaeology,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p. 9, 13-14.
[23] Roberta Gilchrist, "Medieval Archaeology and Theory: A Disciplinary Leap of Faith", in Roberta Gilchrist and Andrew Reynolds eds., Reflections: 50 Years of Medieval Archaeology, 1957-2007, Chap. 1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385-408. Mark Gardiner and Stephen Ripp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Medieval Archaeology”, in Roberta Gilchrist and Andrew Reynolds eds., Reflections: 50 Years of Medieval Archaeology, 1957-2007, Chap. 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70-71.
[24] Ian Hodder and Scott Hutso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3rd ed., Chap.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5-155. [英]伊恩•霍德等著、徐坚译:《阅读过去:考古学阐释的当代取向》第7章《考古学与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3-164页。
[25] Eberhard W. Sauer, “Human History’s Split into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Eberhard W. Sauer ed.,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History: Breaking Down the Bounda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34.
[26] 孟繁之编:《罗泰访谈录:学术•考古•人生》,第32页。
[27] Anthony Snodgrass, “Archaeology”, in Michael Crawford ed., Sources for Ancient History, Chap.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37.
[28] Günter P. Fehring, Translated by Ross Samson, “The Contribution of Archaeology to Medieval Research”, in The Archaeology of Medieval Germany: An Introduction, Chap. 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235-236. German vers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86.
[29] Anthony Snodgrass, “Archaeology”, in Michael Crawford ed., Sources for Ancient History, Chap.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39-140.
[30] Pedro Paulo A. Funari, Siân Jones and Martin Hall, “Introduction: Archaeology in History”, in Pedro Paulo A. Funari, Martin Hall and Siân Jones ed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Back from the 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9, 12.
[31] Matthew H. Johnson, “Rethinking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Pedro Paulo A. Funari, Martin Hall and Siân Jones ed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Back from the 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28.
[32] Matthew Johnson, An Archaeology of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13-14.
[33] Pedro Paulo A. Funari, Siân Jones and Martin Hall, “Introduction: Archaeology in History”, in Pedro Paulo A. Funari, Martin Hall and Siân Jones ed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Back from the 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9-10.
[34] Anders Andrén, Between Artifacts and Text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1998, p. 149.
-

-

-

-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邮编:100871
邮箱:webmaster@pku.edu.cn
-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
京ICP备05065075号-1
京公网安备 110402430047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