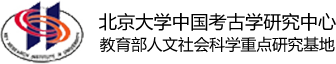优秀论文
返回张弛:民族与革命——百年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
发布时间:2021年7月2日 信息来源:纸上考古
张弛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摘要:中国考古学从诞生开始,研究的取向一直就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历史,另一个是社会历史。前一研究视角试图通过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解决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民族”问题;后一研究视角论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为中国社会的走向寻找理据,在中国近现代话语体系下乃是“革命”问题。民族与革命是上世纪初鼎革之际民族国家的双重诉求,中国考古学于此时应运而生,这两个问题自然也就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史命运。这种与生俱来的、对“文化历史”与“社会历史”的双重追求,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所在。
关键词:民族 革命 文化历史 社会历史
*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批准号:2020YFC1521603)的研究成果。原文刊载于《文物》2021年第6期,作者授权“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刊发,如需引用请据纸版原文。
中国近现代考古学自20世纪初诞生,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不但改写了许多文献历史记载,更填补了史前史的空白。苏秉琦因此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任务”,并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谈,而不仅仅是编写一本书”[1]。其意自然是指在重写史前史的过程中加强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但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究竟有没有自成体系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如果有,又是否有一定的特色,则说法不一。例如苏秉琦认为中国考古学早已成就了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2],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重建的国史不过“只是器物类型和考古学文化的描述和年表”[3]。其实中国考古学涉及的问题和视角既多且广,不从理论、方法与实践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解析,实在难以下一个切实的断语,本文自然也无力解决这样的问题。这里仅尝试从中国史前考古试图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的角度,来探讨学科发展的一个侧面,以期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理解有所助益。
一 两种研究取向与考古学“中国学派”
中国考古学关心以及研究的主要学术方向是什么,这在学界似乎早已有了基本的共识。21世纪以来,很多“中生代”考古学者曾在多种场合表达过自己对中国考古学研究方向的看法。例如许宏近年来就不断申说,“中国考古学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转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4]。赵辉也不止一次提到,中国考古学正在从“物质文化框架转向人类社会研究”[5]。栾丰实认为,“最近二十年来,随着黄河、长江流域等主要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基本建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心逐渐由过去以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为主的年代学研究向社会考古研究转移”[6]。类似的看法不仅出于国内学界,就连西方学术传统中的罗泰也明确指出,“(20世50年代后)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可靠的年代框架……(直到90年代才终于)从无休无止地关注‘时间的形状’转向其他国家的同行们一直感兴趣的实质问题(社会考古学)”[7]。他们一致认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所谓“文化史”(或“物质文化框架”“文化发展序列”“年代框架”),另一个是“社会史”(或“社会研究”“社会考古”),前者是过去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或者需要转向后者,尽管前者仍然是今后研究的内容,但后者终将成为今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方向。
严文明认为以聚落考古为方法的社会考古学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殷墟的发掘,50年代西安半坡发掘则明确提出了从聚落形态分析社会组织和社会形态的目标,但直到七八十年代苏秉琦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也就是文化历史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前提下,社会历史研究才能切实开展。可以看出,严文明同样认为中国考古学有社会历史与文化历史两种研究取向,两者的产生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只是他还进一步认为文化历史研究是社会历史研究的基础,至少在文化历史有积极成果的前提下,才能够进一步开展社会演进的研究[8]。因此在理解社会历史研究与文化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研究取向出现的时间等具体问题上,严文明与上述学者还稍有不同。
其实,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向的完整认识早就已经被明确提出来了。1984年,俞伟超、张忠培在总结苏秉琦考古实践与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指出了考古学“中国学派”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第二是……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感情,有着重要作用。”[9]其中第三点是考古“中国学派”的研究目的,这个目的通过第一、二两条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实现。这两个研究路径中的第一点不仅仅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显然也指的是社会历史的研究取向,意在揭示“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第二点则无疑是所谓文化历史的研究取向,通过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他们明确地指出了两种研究取向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并且认为这两种研究的路径有学术传统意义上的“学派”的独特价值。
许宏、赵辉、栾丰实、罗泰与严文明、俞伟超、张忠培是两代学者,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考古学有两种研究取向,用严文明的表述来总结的话,一种是文化历史研究,另一种是社会历史研究。从定义这两种研究向度的用词上可以看出,他们对前者也就是文化历史研究内容的看法稍有不同,有人认为是物质文化史或文化史,有人认为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或干脆就是年代框架,而苏秉琦、俞伟超、张忠培主张的是从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不过大致的意思应当是相近的;而对于后者也就是社会历史的研究内容,应当是基本一致的。由于这些学者均未对上述看法发表更详细的论证,具体的认识自然不好无端揣测,但隐约能感觉到的一点分歧好像是在于,多数的“中生代”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先以文化历史研究取向为重心,在最近二十年间转向了社会历史研究。而严文明历来都认为两种研究取向早已有之[10],只是社会历史研究需要扎实的文化历史研究为基础。俞伟超、张忠培更是认同苏秉琦的认识,断定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了以这两种研究取向为中心的“中国学派”。
中国考古学为何会有这样两种研究取向?是否一直都有这两种研究取向的存在,还是先有文化历史的研究后有社会历史的研究?如果有先后,是否这两种研究取向的转变是必然发生的,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规律,还是中国考古学区别于世界其他考古学学术传统的特殊现象,是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特有的研究取向?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实践做大量的学术史研究,本文并不能充分展开讨论,以下仅对学界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案例加以分析。
二 不同学术传统的经典研究案例
由学术实践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真正的学术只能是个体性的,由实践者也就是个体学者的研究成果来体现,但个体实践者又非孤立,往往会形成或隐或显的、在学术主张上有所区别的学术传统(或学派)。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些已经“经典化”了的经典学者的经典研究自然也有个体性和传统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个体性的还是传统性的研究,都能够同时看到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两种研究取向。
一直都在倡言“中国考古学派”的苏秉琦一向以所谓“区系类型”学说著称,论者多认为是他发展了类型学或考古学文化的理论,用以阐释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的早期发展,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学说,也就是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但这只是苏秉琦研究取向中着力最多、创新最巨也最引人注意的一面,并不能算是他学说的全部内容。苏秉琦的理想或者说他所认为的中国考古学的“重大使命”是“重建中国史”或“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完成这一使命的初步成果就是由他主编,并与张忠培、严文明共同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他直言“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理想(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续篇)的一块铺路石”[11]。尽管全书由多人执笔,但在《序言》中写明的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前一问题涉及中国境内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后一问题涉及“农业的发生和发展、社会的分化与分工、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以及历史的传说与真实”,真正的核心正在于社会考古学。不过这部著作很难说完全是他个人的思考。完整的想法应当体现在他晚年重建中国古史的纲领性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该书开宗明义提出想突破“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12]。对前者的突破就是他自己的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学说,研究方法则是他自己的区系类型,以多元起源论证明了大一统是后来的观念。对后者的思考正属于社会史的向度,他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三部曲、三模式,即古国、方国、帝国(更早的提法是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原生型(燕山南北)、次生型(中原)、续生型(北方)三模式,试图概括中国早期社会发展的历史,希望以中国社会具体发展的道路来阐释马恩的普遍规律[13]。
师承苏秉琦的张忠培,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时称:“我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一个是考古学遗存所表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变化。”[14]他最信服苏秉琦文化谱系学说,以至于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考古学文化”[15]。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始终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从早年对仰韶文化分期、类型等问题研究开始,直至近年来对陶鬲谱系的研究,最为着力的论题涉及了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全部的区域和新石器时代—商周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而还总结出考古学文化“历史—文化区”和“亲族考古学文化区”两种文化关系的模式[16]。另一方面,张忠培学术研究的成名作却是《华县元君庙》,从元君庙墓地的分期、布局以及人口结构推定了仰韶社会母系家族和氏族社会的组织形式,开启了“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而这一研究意图其实是在1958年发掘元君庙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的[17]。随后,张忠培还论证了黄河流域仰韶时代从母权制到父系制的转变、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社会权力形态等诸多的社会历史问题,进而对中国文明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阶段做了全面总结,并曾结集为《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一书[18]。
严文明并不执着于“中国考古学派”的提法,但始终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他早期代表作《仰韶文化研究》前言中就特意强调“我的文章不只是就事论事,还很注意有关理论和方法的探索”[19],该书虽为论文集的形式,但显然自成体系,可以分为两条清晰的线索,一是从典型遗址的分析入手,渐次讨论整个仰韶文化的分期、类型、起源、发展阶段以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二是从姜寨、横阵等典型聚落和墓地分析入手,进而全面探讨仰韶文化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这两条线索正是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的两种研究取向。在前一研究论题上,严文明随后还发表过多篇区域文化分析的文章[20],以及如《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等综论性文章[21],最终总结为《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22],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重瓣花朵”模式并发展为多元一体学说。在后一研究论题上,倡导利用聚落考古方法探索史前社会,组织了“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重大课题,对中国史前聚落与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23],并有总结性文章《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24]发表。
明确否定苏秉琦“中国学派”提法的则有夏鼐和安志敏[25],他们并非不期待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而是对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发展中是否有自身的特色有不同的考量。在学术实践上,20世纪50年代夏鼐最早规范了考古学文化的用法[26];安志敏将仰韶文化区分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27],积极推动中国史前考古中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夏鼐在80年代发表《中国文明的起源》[28],明确指出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从殷墟一直上推到新石器时代,虽有外来影响,但无疑是独立起源的;安志敏则更是明确一贯坚持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民族起源一元论[29]。这些研究显然是文化历史的视角。夏、安两位学者在史前社会历史研究方面虽然没有特别多的着力,但夏鼐主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30],应当能够看作是夏、安两位特别是夏鼐的体系性思考。该书以考古学文化分区分期为经纬,在资料丰富的区域如黄河流域的叙事中则专门论及经济形态、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显然是继承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体例,其中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仍然以考古学文化区系为纲领,再加上经济技术、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三个部分[31]。与夏鼐有师承关系的石兴邦则在两个方面都有实践,1980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问题》是他长期文化历史研究的总结[32];而早在50年代中期,他主持半坡遗址发掘并第一次有目的地大面积揭露史前居址时,发掘报告副标题就特意标明“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33],开启了从聚落入手研究史前社会的途径[34],成为此后由聚落研究史前社会的典范。
上述无论是提倡还是拒认“中国考古学派”的经典研究者,都包括了前后两代学者,他们的研究经历几乎纵跨整个中国考古学百年的历史,直至当下。他们研究的取向都是兼具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两个方面。因此,可以说这两种研究取向,其实是中国考古学一早就设定的。
三 为何是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国人自古以来天下国家的执念随之幻灭,中国国史千古一系的观念发生动摇。在西方盛行一时的传播论之下,中国文明、中国文化西来说逐渐盛行。不宁唯是,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更引出了古史辨派学说,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上古帝系应当归于传说,甚至夏代也不大靠得住,商代以上的历史遂成为空白。接续国史,不得不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学。
期间,中国境内史前遗址和遗存虽屡有发现,但真正引起学界和国人重视的显然是安特生于1921年发现和发掘的仰韶文化。囿于当时有限的材料,安氏不得不将仰韶的发现与更为遥远的中亚、东欧如土库曼安诺、乌克兰特里波列(特黎波里)遗址进行对比,于1923年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35],认为仰韶这样一支彩陶文化是中国史前期的远古文化,其来源很可能出自中亚一带,为了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随即施行了他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可以说安特生在仰韶和甘青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揭开了以近代考古学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新的一页。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也因此流行一时[36]。
安特生研究中国远古文化未必是为了续写中国国史,但随后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发掘西阴村和殷墟则舍此并无他图。史语所1930年发掘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之后,仰韶和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学说出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破产”[37]。1949年前史语所对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更是揭示了商代晚期灿烂的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郑州商代早期遗存以及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发现和发掘,使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主流[38]。随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更多发现,促成苏秉琦在70年代提出了“满天星斗”的多元起源论,并在此后,发展为学界多数人接受的“多元一体”起源学说。这一研究取向,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何时、何地及如何起源的,其理论与方法正是本土化的“文化历史主义”。
仰韶遗址和殷墟遗址的发掘,固然使1921年和1928年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都具有了纪元元年的意义,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更具历史象征意义的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和建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先是国共两党合作北伐,继而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国共产党不得已开始了独立的军事斗争。而两党乃至整个知识界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论争也就此达到顶峰。为了论证中国社会发展前途,也就必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加以阐释。最为突出的研究案例,是亲身参加了大革命并在大革命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他在1929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9],按照苏联式社会发展史(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旋即在整个知识界出现的“社会史大论战”,正是因应这一时代的历史潮流[40]。
要获得对中国社会现实与未来的清楚认识,不得不回看历史,社会史大论战的出现乃是历史的必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刚刚开始,没有多少可以用来研究古代乃至史前社会的材料,对于商周社会,郭氏及其他研究者不得不止步于甲骨金文的材料,史前社会的研究,虽有尹达在延安时期撰写的《中国原始社会》[41],但并没有多少社会史的实际内容,以至于后来此书改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在50年代出版时,尹达仍然感叹于史前社会考古材料的缺乏[42]。
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五朵金花”(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为研究的热点,其中除汉民族形成问题在考古学上是利用文化历史研究来考察以外,其余四个都是社会史的议题,历史时期考古自不能例外。在商周考古领域中利用墓葬材料研究古代社会已成风气,郭宝钧对浚县大墓的分类显然就是为了说明社会的分化[43],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也讨论了三代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关系的问题[44]。在苏联通过全面发掘特里波列聚落研究史前社会的方法影响下[45],大规模发掘并完整揭露半坡、元君庙、横阵和姜寨等仰韶文化的遗址和墓地,研究仰韶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一时成为风尚,至20世纪90年代仍是史前社会史研究的热点。1959年,大汶口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当时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报告的发表引起了对大汶口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热烈讨论。最为激进的研究者如唐兰,甚至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奴隶社会[46]。80年代前期,红山文化“坛、庙、冢”和良渚文化瑶山、反山墓地的发掘,引起了中国古代社会和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至今不衰。由此可见,考古学一直是中国远古和古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自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国家和中国社会的多重危机,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社会变革的要求无法分离,民族与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化首当其冲的核心问题。不论是国共两党还是代表不同阶层的其他政治势力都提出了自己的民族与革命的愿景,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只是民族问题基本有共识,革命问题则难以达成一致,所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各党派才有联合、有分裂乃至内战。民族与革命的实践必须有理据,中国近代历史学乃是为了解决中国由何处来、又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而出现的。中国近现代考古学自不例外,要回答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也就自然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两个主要的取向。
四 中国考古学特色何在
从学术传统、个体实践以及发生背景等多个角度来看,俞伟超、张忠培在1984年对中国考古学特点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研究两种取向确实一直都是中国考古学的追求,但这两种研究取向是否构成“中国考古学派”独特的研究视角却需要进一步的分辨。
所谓文化历史考古,乃是以考古学物质文化定义“文化圈”,在有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时期,则附会以古史记载的族属,这样“物质文化圈”便成为“民族文化圈”的替代品,于是追溯“考古学文化”便可以成为寻找古代民族来龙去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西方考古学传统中一般认为始自德国历史语言学家科西纳,后由柴尔德发扬光大。1926年,柴尔德出版的《欧洲文明的曙光》是其集大成之作[47]。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安特生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同时也有研究者论证了仰韶文化就是虞夏文化[48]。此后,本土化的文化历史考古虽然被称为“区系类型”学说或者文化谱系研究方法,但按照俞伟超、张忠培的说法无非就是“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49]。而三代考古至今仍然热衷于利用考古学文化、文化谱系或文化因素来探讨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进而“追迹三代”[50]。这种研究范式与西方近代考古学并无不同,更何况在中国考古学中,最先规范考古学文化的夏鼐,利用的就是柴尔德考古学文化的概念[51]。
中国社会史研究始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5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本来就是试图写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只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包括了苏联式的社会发展史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进一步受到苏联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开始研究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和社会意识。史前考古的社会人类学理论,则主要来自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53],论证史前由旧石器时代原始群向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和军事民主制的发展规律成为很长时期内史前考古的任务。而西方首倡社会考古学的柴尔德本人也是受到苏联考古学的影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随后在西方考古学中出现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派,由于利用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一般被归于新考古学的阵营。因此,中国考古学无论文化历史研究还是社会历史研究都不能说有别于西方考古学。
西方考古学理论,一般被总结为进化论考古学、文化历史主义、新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四个发展阶段。进化论考古学,以丹麦学者汤姆森的“三期说”为首倡,同时也是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出现的时间甚至早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考古学的文化进化体系最早在欧洲建立,成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奠基石。科西纳和柴尔德利用考古学文化研究欧洲古代族群的变化发展,开启了文化历史的研究途径,显然是对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首先出现的合法性诉求的回应并为之提供法理依据。宾福德提倡的新考古学,意图寻找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二战后科学至上、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发展时期的结果。而后过程主义反而认为人类历史并没有普遍的、共通的发展规律,是为后殖民时代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背书。
文化历史考古与社会历史考古背后的理论并非国产,而是近代以来首先在西方出现并迅速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和文明论,中国考古学显然没有自外于这个历史大趋势。但中国考古学与上述西方考古学理论发展的线索又不完全合拍,还与中国近现代史背景、中国的史学传统乃至西方考古学传入的时机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国考古学既有与西方考古学暗合的研究取向,又有发展的特定线索。中国考古学的出现晚于西方上百年,一开始就有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两种研究取向,尽管期间有交流的中断,但在研究的取向和理论上与世界考古学并无隔膜。这也可以算作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中国考古学发展起来的文化历史研究方法是所谓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与谱系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社会历史研究则为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后来还有西方社会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考古学,多利用手工业、墓葬和聚落形态分析方法。这两套研究方法还缺乏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以致近年来史前考古凡是以“文化与社会”为题的研究论述都不免有“两张皮”之嫌,并不仅仅是有些具体研究简单粗暴、生拉硬套的问题。正如近现代历史中,民族与革命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天然的张力一样,单就文化历史与社会历史研究的问题本身来看,二者之间本应有内在的联系。文化历史研究“民族”的来源与“民族关系”,是取自社会外部关系的角度;社会历史关心社会阶层、社会关系和社会革命,则是社会内部的问题。因此就学理上来看,两个视角也不是不能都归结到社会层面上来。
五 结语
中国考古学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当代政治历史孤立发展。中国考古学从诞生开始,研究的取向一直就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历史,另一个是社会历史。前一研究视角试图通过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解决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民族”问题;后一研究视角则大多数时间按照苏联式社会发展史观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史,为中国社会的走向寻找理据,在中国近现代话语体系下乃是“革命”问题。20世纪初,中国历史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与革命乃是鼎革之际的双重诉求,中国考古学于此时应运而生,这自然也就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命运。这种与生俱来的、对“文化历史”与“社会历史”的双重追求,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所在。只是从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研究的两种理论与方法还缺乏内在的联系。
注释:
[1]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2] 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后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3] 陈淳《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4] 王巍等《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考古〉的历程——纪念〈考古〉创刊60周年笔谈》,《考古》2015年第12期。
[5] 赵辉等《新形势、新需求、新规程:新修订〈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相关说明》,《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6] 栾丰实《编写一本反映中国考古学实际的教材》,《光明日报》2015年9月10日。
[7] [美]罗泰著、吴长青等译《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8] 严文明《前言》,《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2015年。
[9] 俞伟超、张忠培《探索与追求》,《文物》1984年第1期;后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 严文明《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11]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2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13] 李新伟《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第10~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4] 张春海、耿雪《张忠培:透物见人,考古求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8日。
[15] 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6] 张忠培《编后记》,《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7] 严文明《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元君庙仰韶墓地〉读后》,《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
[18]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9]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第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20] 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21]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22]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3]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2015年。
[24]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5] 安志敏《论环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评“区系”观点》,《考古》1993年第7期。
[26]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27] 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28]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29] 安志敏《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文化源流的思考》,《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2期。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2] 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年。
[3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34] 同[10]。
[35] [瑞典]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1923年。
[36]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30~13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37] 同[36],第302页。
[38] 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主要成就》,《文物》1959年第10期。
[39]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新书店,1930年。
[40] [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58~2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41] 尹达《中国原始社会》,作者出版社,1943年。
[42]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43] 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4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45] [苏联]T.C.帕谢克、石陶《特黎波里居址的田野考查方法》,《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46] 唐兰《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
[47] [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第181~1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8]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49]同[9]。
[50] 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51] 同[26]。
[52] [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53] [苏联]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
-

-

-

-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邮编:100871
邮箱:webmaster@pku.edu.cn
-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
京ICP备05065075号-1
京公网安备 110402430047 号